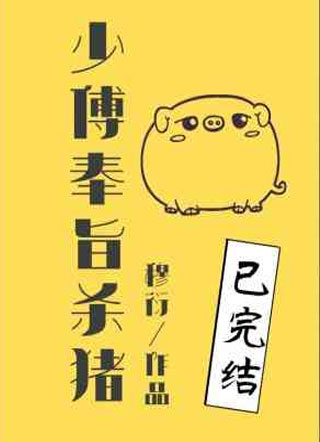
时间:2023-06-21 来源:长佩 分类:现代 作者:穆衍 主角:付栖 郑以山
郑以山的屋子只有一间,勉强用一道木栅栏隔出内外间,栅栏上搭着几件半干的亵衣,旁边还钉了一个歪歪扭扭的书架,放着一摞泛黄的草纸。
付栖一手扣着郑以山的手腕,把从他身上搜出来的鬼话放回书架中,信手翻了下余下的草纸,确认其中没有夹带,才抬头往四周看去。
郑以山看起来过得颇为清贫,屋中家具也没有几件,收拾得倒是干净,窗台上摆了两盆葱苗,长得郁郁青青,就是葱尖被人薅秃了一块。
这屋子简陋得一眼望得尽,付栖转了一圈,把视线挪回郑以山身上。
郑以山挣不开他,被他拖着手腕在自己屋子里走了个来回,眉间透着股不耐,怒道:“你个莽汉!追上来撒什么酒疯?嫌昨晚活不够爽利吗!”
付栖没吭声,他的目光在郑以山的衣襟间停留了一会儿,眼睛里写满了慌张。
郑以山被送到付栖床上时被扒了个精光,也不知道他那身寒酸旧衣被丢到了哪里,只能光着身子套付栖的外袍。领口和袖口都有些大,露出一截白皙脖颈,昨晚回家路上被蚊虫叮了,肿块还没消,红痕浅得可疑。
付栖不自觉地盯了一会儿,想起昨晚看到的漂亮细腰,喉头忍不住微微一滚,被郑以山冷笑了一声,指着门简洁道:“滚!”
郑以山还想把手腕抽出来,只是力气不必付栖,只叫他指腹一滑。
付栖在营中和人勾肩搭背惯了,原本没想什么,被郑以山骂上两句,反倒能感觉出手底下那段手腕的柔软触感,力道不免轻了三分,一面道:“我是来送你的工钱的。”
郑以山把碎银收到匣子里,想了一下,又摸了五枚铜板出来,从门口茶棚买了壶粗茶,留下两文钱当借走茶具的抵押,进门来给付栖斟了茶,心平气和道:“工钱在这了,我的衣物和刀呢?”
杀猪倌的家伙事里有几把能砍断骨头的利刃,都被官府登记在册,每月检查,郑以山本想着把草纸送去说书先生那里再去讨要,就被付栖抢了先。
付栖道:“晚上我叫人送来。”
他没接郑以山推到面前的茶,抬手叫了一名手里提着棍子的亲兵进来,双手托着向郑以山一揖,沉声道:“栖御下不严,惊扰百姓,理应受杖八十。”
郑以山的眉头扬了起来。
他过去虽然是个典型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但被流放到边关后迫于生计,也练出了一身单手扛猪崽的本事,挥几下军棍轻而易举,保证能把付栖揍得哭爹喊娘。
然而他在脑中想了一下场景,再一抬头对上付栖那张素有“玉面”美名的脸, 不知道为何突然有点索然无味,摆手道:“屋里施展不开,你出去打,记得小点声,别吓到我的猪。”
付栖带了亲兵来,原本也没想要劳烦郑以山,他将手垂下,心不在焉地应了声,拎着棍子出了郑以山的屋子。
院中因为隔了一个猪圈出来,留给人活动的地方也不太多,只有窗下有一片空地,文人气地养了两盆兰草。
付栖把兰草搬到一旁,在旁边猪崽好奇地哼哼声中褪下外袍往腰间一系,手肘拄着窗沿弯下腰,一面示意亲兵动手,一面隔着窗户对郑以山说:“原本应当把那几个混账叫过来观刑,但我想着你或许不愿再同他们打交道,就没把他们叫来。”
郑以山坐在椅子上整理被翻乱的草纸,闻言走过来放下窗扉,皱眉道:“也别吓到我的葱。”
因此最后看到付栖挨揍的只有郑以山养的猪崽。郑以山回来后还没来得及收拾它们,都在窝里滚了一身泥,有的还剩一个粉鼻子没有裹上泥浆,看到从付栖手肘上滴下来的血,拱着鼻子探过栅栏闻了闻,又失去兴致地走掉了。
郑以山对窗外传来的动静充耳不闻,他垂着眼睫,慢腾腾地一张张翻看膝盖上的草纸,看到中间时手下微微一顿,把那张纸抽了出来,正要撕碎丢进泔水桶中喂猪,忽然听到付栖敲了一下窗框。
他下意识地将手中的草纸夹回纸摞中,付栖的亲兵就推门进来,将那叠草纸从郑以山手中拿走,顺势把他押出了屋。
付栖的八十军棍还没打完,里衣已经碎了,满背皮开肉绽,鲜血淋漓。郑以山看了一眼,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眩晕,赶忙收回视线,听到付栖用若无其事地语气问他:“你要通过谁和太子联系?”
郑以山装聋作哑不肯回答,付栖也不多问,皱着眉挨完八十军棍,将系在腰间的外袍一解搭在栅栏上,抬手招呼亲兵上前为他裹伤。
他生得是肉体凡胎,但在边关镇守几年,倒也算是磨练出一副钢铁铸的筋骨,竟像伤不在自己身上似的,面不改色地抬臂穿上外袍,用手背擦了一下唇边的血沫,站直身体,转头吩咐亲兵道:“把这根棍送去营中,叫那几个把它刷洗干净,一人分一截去。”
亲兵应了“是”,把用过的伤药瓶子收进怀中,拎起立在窗户边的军棍,向付栖行了一个礼,低头退出郑以山的院门。
门打开的时候不远处的茶棚中隐隐传来一声:“且说那付将军——”
付栖似乎想要抬手揉一下眉心,但手腕抬到中途突然顿了顿,脸上露出一点苦恼之色。
郑以山显然也听到了门外茶棚传来的动静,他的目光挪向被另一个付栖的亲兵拿在手中的草纸,再看了看付栖的面色,笑道:“我这评词比昨夜那诗如何?”
郑以山是年少成名,当时诗句中意气重,侠气动京华,但也透着股不肯落凡尘的骄矜桀骜劲。
付栖虽与他并称,却是结结实实地从小吏做起的,两人以诗句酬答时没少讽刺郑以山是个只饮晨露的闺阁娇儿。虽不知郑以山究竟是在何时变成了眼下这幅脾性,闻言只道:“宣之倒是终于肯写些俗事俗务了。”
宣之是郑以山的字,他抱起胳膊,懒洋洋地说:“我这是在救你,凤凰儿。”
付栖小字竹竹,加冠后因名取字,就唤做凤凰。
他和郑以山同龄,在京中时也算地位相当,虽然看彼此不顺眼,私下里“娇娇”、“莽夫”胡乱编排,当面交谈时也是互称表字的,只是不曾在后面加一个轻佻的儿化音。
付栖唇边还有一点血痕,叫他看起来有点绮丽颜色,但他沉默一会儿,没有说话。
郑以山侍奉的那位太子殿下一向谨慎甚微,素有孝心,只是身上多了些贤名,又有两三件事与皇帝的心意相悖,就被生生扣上大不敬的罪名。
而付栖带兵在外,力保边关不失,尚有余力率军将来犯的赫羯人赶出二百余里。在关外逡巡,吓得赫羯祈和进贡,无异于往主和二十余年,甚至忍痛嫁了位公主的皇帝脸上吐口水。
以那位的性情,只怕是要寻机杀了付栖才会满意。
郑以山身上没有方巾,想到此处,就从亲兵手中抽了一张草纸出来,翻到没字的那一面揉成一团,往付栖唇上一蹭,又随手丢进猪圈中。
付栖的唇瓣被草纸擦出一层血色,他怔了一下,没注意自己被郑以山岔开了话题,答道:“我知道此次必死,想着叫赫羯多安分几年,才一直在关外多。你是文臣,即使没了功名,起复也不难,何必为我坏了自己名声。”
付栖从郑以山的院子离开已经在两个时辰之后,中途他的亲兵离开一趟,把郑以山吃饭的家伙事拿回来,还附赠了一刀宣纸。
他回来的时候街上正热闹,茶棚中挤满了人,说书先生把“付将军提枪上阵打得郑屠户两股战战”说了十几遍,不仅没有厌烦,反倒紧跟时事,推陈出新:“那营中将军因对他心爱之人强取豪夺,挨了好一顿胖揍呐!”
亲兵情不自禁地在茶棚前驻足,听了两三段,付栖遣人出来找他,一并被认出来,又惊又喜道:“将军也在这里?”
郑以山随手熄了火,挪走架在膝间的磨刀石,将杀猪刀立在凳子边,起身送付栖出门。
栅栏后的猪崽刚得了投喂,哼哼着挤在一起,付栖留下的血迹被他的亲兵打水冲干净了,地上有些湿,他从窗下站起来的时候漫不经心地提着袍角,看姿态还有些风流气。
付栖正要和他拱手告辞,目光不免在他提着袍角的纤长手指上停留片刻,然后挪到了被衣带束得看起来不盈一握的腰肢上。
郑以山惯来是个养尊处优的细腰文人,付栖早知这一点,然而许是时移境迁,近来他看郑以山总是心思浮躁,倒没有往日非要与他分个胜负高下的念头。
他定了定神,婉拒了郑以山送他出门的打算,郑以山就只叫他搭着自己的胳膊出了院门,站在门内向他一揖,忽而正色道:“将军力挽狂澜,救民危难之中,远胜我等词臣,还望珍重。”
付栖正要应答,忽觉身后安静得吓人,回头去看,只见来时还满客的茶棚已经空了,只剩一个穿着长袍握着醒木的说书先生,喃喃自语道:“这竟不是话本吗?”
“付将军强纳郑屠户,还大街小巷都传遍了。”皇帝托着下颌饶有兴趣地问,“这是从哪冒出来的流言?”
他面白无须,眉眼细长,是个颇阴柔多情的相貌,只是唇边总噙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透着点乖张狠戾气,叫人看了总觉得不寒而栗。
向他汇报的太监埋着头跪在地上,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了,仍然一动也不敢动,听闻皇帝垂询,连忙恭声道:“据查是郑以山为求糊口写的话本,后来有人见到付将军从他院中出来,就引以为信……”
皇帝轻笑了一声,打断他道:“荒谬。”
郑以山生得一副风流相,处事上却是个再正经不过的君子,便是与付栖相看两厌,平常写诗对骂吵得人尽皆知,他要将付栖贬做校尉的时候还上表给他求过情。
皇帝当时觉得有趣极了,就又给付栖加了一道旨意,叫他终身不得返京,与家人永隔两地,又派人暗中在付栖左近阴阳怪气地议论说:“听说郑少傅给陛下上表替那姓付的求情,说什么‘今日夺侍郎之文名,恐来日无书生报国’,这不是适得其反吗。”
郑以山是做不出这种不要颜面的事的,想来是付栖嫉恨郑以山害他,要毁了他的名声。
皇帝沉思一阵,拊掌笑道:“来人,拟旨,朕要为他二人赐婚。”
郑以山拖家带口地搬到将军府隔壁的时候付栖才养好伤,不必每日面对老大夫的冷面,就迫不及待地带着酒去寻郑以山作诗。
郑以山养的猪崽又胖了一圈,被捆了四蹄倒放在板车上拉过来,因为猪圈的栅栏还没钉好,只能暂时摞在院子中,不知道是哪个闲来无事,把不满地呼噜着的猪崽们摆得整整齐齐,害得付栖一进院门险些以为自己看到了什么阅兵列阵的大场面。
他脚步一顿,目光在院中搜寻一圈,找到了弯着腰抡锤子的郑以山,就放下酒上前帮忙。
郑以山今天又穿了一身破烂短打,手腕和脚踝都露在外面,腰上也有两个补丁,缝得不太好,他敲钉子的时候除了脚踝上浮出漂亮的淡色青筋,还有一截白皙得令人眼晕的腰身。
付栖晚上在席间喝得微醺了,忍不住作诗称赞说:“风惊柳腰软,雪压花稍细*。”
这诗隔日就被郑以山写进了话本中,来边关传旨的钦差入城时道两侧各有一个站着说书先生的茶棚,一个说“风惊柳腰软”,另一个说“拈梅点雪声声轻”,全都是上不得台面的淫词浪语,叫面皮薄的姑娘听了掩面而走。
*《三刻拍案惊奇》
钦差原是付栖的同年,付栖中了探花,他发挥不佳,只得了个三甲同进士。这人好使性子,怪罪付栖作答太快扰了他的思路,才叫他没高中,一直心有怨气,因此皇帝点了他去边关宣旨,还嘱咐他一定要把婚事办得热热闹闹。
付栖负手立在城门口等候钦差,见他拿出符节等物,便屈膝行礼道:“恭请圣安。”
钦差回答说:“圣躬安。”收起符节扶付栖起身,等他站直转身,要引他往城中去时,又取出赐婚的圣旨当众宣读,最后含笑道,“陛下体念将军清贫,赐下财帛,又嘱咐我一定要为将军主持了婚礼再走。将军快些谢恩吧。”
边关的文臣长官在去年赫羯来犯的时候弃城而逃,宁可被吏部连记了两个考评下下都不愿回去履职,其余文官一听要被调派到边关为政也都纷纷告病推辞,付栖就不得不暂代文职。
他做的是货真价实的封疆大吏,皇帝的赐婚并非自己求来,旨意后面代表的不是爱重,而是试探和羞辱,何况被被赐婚的另一人是郑以山。
他和郑以山在京中的骂架称得上人尽皆知,虽然如今年纪渐长,关系缓和了许多,想起当时年少轻狂的荒唐模样,常哑然失笑,可天下人并不知情,连郑以山写来糊口的话本都被删改成了“付将军强取豪夺郑屠户”。
他已打定主意为国赴死,这道旨意接不接无关紧要,但总不能牵连郑以山因他丧命。付栖沉吟片刻,俯首一叩,双手接过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