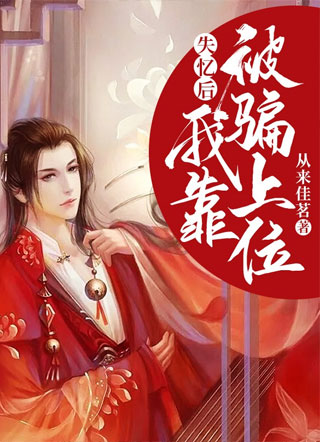
时间:2022-10-19 来源:一纸 分类:古代 作者:从来佳茗 主角:江景 徐衍
这个年真的是让许多人都没能过得安生。
京城里的各大势力原本就盘根错节,复杂难理,现今又来了位身份尊贵的长公子,甚至陆阁老也明晃晃地站在他跟前护上了。
祁镇翊登基时间也不算短,期间也做了几件荒唐事,尤其是两年前私下在科举上动了手脚,伤了几个世家的根基,不仅叫世家望族不齿,也叫寒门难堪。
这事说来实在荒唐,大悦历次科举学子中举之数世家与寒门草草可作七三之分,这三分寒门中又大多依附世家,余者四散在地方,有资格入朝留在崇政殿上的实在寥寥无几。
祁镇翊想要养一帮能和世家叫板的寒门心腹出来,帝王权术,他会有这样的想法本也无可厚非。只是乱世百姓本就生计艰难,读书并不兴旺,寒门少才子,当真惊才绝艳的文章与人物又能有多少,难不成还为了硬挑寒门而改变科举规则吗?
咱们这位帝王的天真就在此处,他不行法令,不改规则,却悄悄授意主考的官员私下换了考生的卷子,生生提拔了几个寒门出身的人上来做了进士,这原也没什么,即使是世家贵族,谁能说自己就从来没在科举上做过什么手脚呢?皇帝做这样的事情,虽然自降身价,却也没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可这事坏就坏在这批寒门之中有个叫沈风的,是个十足的死脑筋。
旁人被换了卷子,遭了提拔都感恩戴德,觉得是自己祖上积了德,没有不藏着掖着的,只有这个沈风竟然将这事捅到了大理寺,说要告科举考官玩忽职守,连考生的卷子都能判错,还要求彻查考生考卷,一定要为皇上选出真正的人才。
皇上当时在崇政殿看大理寺卿的折子,看得脸都绿了,这哪里是能彻查的事,姓沈的要查谁?查皇帝么?
既然不能彻查,只得草草了结了,将几个考官撤了职,牵一个出来认了罪,那几张换了的考卷却万万不能查出来的,这几人虽也中了举,却因此事让皇帝心虚,到底不得重用,远远地打发去地方了。
事情到这里还不算完,几个有名望的世家牵头夸沈风刚直有风骨,是个不为名利折腰的人,要皇帝破格将他封做翰林,留在朝廷听用。
祁镇翊恼羞成怒,命将此人由大理寺移至刑部再查此案,最终将此人判罪下狱,牵连家族中人一并流放北境。
当今皇帝在一众老臣中的威信原不是很高,这也难怪,他原本就不是先帝属意的继承人,先帝不爱美色,膝下子女不算多也罢了,文武都不见有佼佼者。
先帝恨他的儿女不争气,在当时还是长公主的祁姝华没成亲之时就曾戏言她性子厉害,定能教出个惊才绝艳的孩儿来,到时好生与驸马商量,将他们的儿子赐了祁姓,送进宫里来养。
长公主性子恣意,不觉长兄出格,倒乐得同他玩笑,直言她的儿子,自然是随她走江湖的。
这原本是皇家兄妹私下调侃,却被先帝当做轶事说与臣下听,先帝仁爱,与臣子谈及私事不会叫人生惧,当时几个在场的臣子还笑言圣上九五之尊,君无戏言,先帝也应了的。
史载,帝允诺长公主,“将来汝之子,赐祁姓,上皇室玉碟,视若皇子,一般无二。”
可是祁镇翊怎么敢让江景姓祁,他原本就是仗着自己是先帝唯一仅剩的嫡亲血脉稳住了位子。何况当年大长公主夫妻二人大权在握,不知给后人留了多少人脉势力,且江景又身在江湖,同江湖世家关系紧密。
祁镇翊心里原本就有很多刺,现今又多了一根。
“皇上也不必太过担忧,或许真的只是个意外呢?”
御书房内,屏退众人,祁镇翊坐在桌案后面,底下跪着的是户部尚书王宽,他跪着好半天了,只不过皇帝一直没叫起,祁镇翊脸上的焦躁之色愈重,他愈胆战心惊,不由出言宽慰。
“意外?还能有什么意外?且不说这人刚认回来,他陆从宜就火急火燎的领回家去,生怕放在外面会有什么人害他似的,就是这老家伙在麒麟街上认出江景的事朕都觉得巧合至极,陆从宜说他身子弱,多少年不出门了,出去一次就刚好去了麒麟街,去了一次就恰巧撞上了江景,世上哪有这样巧的事?”
祁镇翊听不进旁人劝解,他现今满脑子都是引狼入室,玩火自焚的典故。
“朕还要替他封王改姓,他日后又当如何?”
王宽觉得皇帝心胸未免狭窄又多疑,但他丝毫不敢表露,甚至他还得感谢祁镇翊这样的性子,否则他就永远没有机会跪在这,寒门科举难,他虽不是被换了考卷进来的,但若不是皇帝,也早就被发配到偏远地方做县官了。他是祁镇翊头一个提上来的寒门,磋磨了多少年才熬到户部尚书的位子,必得紧紧靠着皇帝这棵大树不可。
“皇上若见了他实在心烦,不若叫他去戍守南疆,当日霍大帅上折子,字里行间不也是这个意思?”
“大长公主同翟措的嫡长子,朕的亲表弟,流落在外二十二年,刚回京城,朕就让他去守南疆,王宽啊王宽,你叫那些朝臣怎么看朕?百姓又怎么看朕?”
“皇上莫急,臣并非此意,皇上仁爱,虽先前有意为长公子封王改姓,但既然于理不合,多受诟病,不若就改封为侯也是无奈之举,长公子武功高强,又多年身在沙场,颇有良将之风,且让长公子在京城多留几年,届时南疆无人镇守,他便成了最合适的人选,纵然皇上不任命,长公子忠君爱国,难道还不请缨?”
王宽引着皇帝这般想着,祁镇翊也渐渐放下心来,想来也是,他二十多年不曾踏足京城,纵然一时身份尊贵,又能掀起什么风浪?他神情一松,忽然注意到底下还跪着的王宽,
“爱卿起身吧,怎么朕一时没注意到,爱卿自己也不说?”
王宽暗诽他一个臣子能说什么,他的腿脚已然跪麻,却还要缓缓起身,控制着不能颤抖一分一毫,面上不敢露出丝毫怨色,甚至还表现得无比真诚,“臣为皇上排忧解难,一时竟也没注意到。”
祁镇翊听得高兴,大笑,“朕知爱卿之心。”
说完既觉江景翻不出什么风浪,替自己的表弟封个侯也就不那么难受了。
王宽看出皇帝心急,想将这件事早早定下,他也有意让人知道自己对皇帝的影响力,添一添自己在朝中的分量,于是刻意问道:“不知皇上要为长公子定下何种封号呢?”
“此事急切,叫礼部拟了来看既耗费时间,也看不出朕的心意,他生长在沉阳,那处多江河,称为津洛一带,不若就拟定平津二字。”
祁镇翊沉吟,提笔写了旨,盖上了玉玺。
御书房外候着的是个小太监,远远瞧着他师傅景安,也就是祁镇翊一直用着的大太监过来了,不由问道:“师傅,这皇上的心情怎么见天儿的变着,方才王大人进去的时候还是阴云密布的,现今听着里头的声音,又龙颜大悦了。”
景安给了那小太监一个脑瓜崩儿,“皇上的心情,也是你这小崽子该揣摩的,好生伺候着比什么都强。”
那小太监摸着自己的脑袋作势,“哎呦!”他看着景安笑着奉承,“皇上的心思还得是师傅来猜。”
景安高兴,难免多提点他两句,“你呀,多瞧瞧殿里的那位王大人。”
“景安!”里头突然唤他。
景安于是匆匆叫那小太监“少贫嘴”,又收敛了神色从容地进了御书房,“皇上?”
“去,去传朕的旨,长公子幼年流落在外,少失恃怙,朕意既怜且哀,着封为平津侯,且作……正二品。”
说着,祁镇翊又想到了什么似的,补充道:“给他的府邸不要用侯的品级,朕记得前朝安南王府还没做用处,休整一番给了他吧!另……黄金绫罗,珠宝财物,也都按封王的礼节赏他。”
一旁站着的王宽朝景安递了个眼色,景安立时心领神会,“皇上仁德,平津侯定然喜不自胜,对皇上感激涕零。”
为表皇帝心意,景安亲领了这传旨的活计,王宽同着他一并告退,
“王大人在皇上心目中的分量愈发重了,今日封侯的圣旨都是在王大人眼下出来的,可见皇上倚重信任大人。”景安身材臃肿,笑得时候脸上的褶子堆起来。
王宽笑道:“公公折煞我了,怎么也不会比公公在皇上跟前更得脸。”
两个人并排往前走着,眼见就要到了宫门口,王宽想起一事,斟酌着探景安的口风:“公公,听说前日里皇上召见了青云观的道士,不知……”
景安自然知道王宽欲问何事,这自古啊,皇帝身边最亲近的无非就是那么几类人,第一是宦官,不是他景安托大,他自己便是皇帝身边最得用的宦官;第二是妃嫔,当今皇帝随了先帝的性子,后宫妃子也并不多,却到底比先帝强些,除了皇后,四妃九嫔好歹满了半数,底下美人,采女等也不很少,只是不见有哪一位分外出挑,能独得盛宠的……不,也不是没有,当时翟德妃确实最得圣心,张扬跋扈,不也没过几年就出了事香消玉殒了吗?景安鄙夷地摇头,接着往下数,若是皇帝偏好哪一派宗教,便少不得要提一提这和尚、道士,历朝历代也不是没有信教的君主。
皇上年前召见了青云道长,景安琢磨着祁镇翊的性子,向来不看重这些。
“我瞧着,皇上也没有宠信青云观那帮道士的意思。”
“多谢公公提点。”
陆府。
江景在前堂规规矩矩的接了旨,听景安说了几句讨喜话,“恭喜侯爷,贺喜侯爷,侯爷您在外吃了苦,总算是苦尽甘来了。您现下啊就在咱们皇上心尖儿上,有什么难处尽管向皇上提,骨肉血脉如何能不亲近呢?”
江景虽难解这苦尽甘来,只怕是苦还未尽又添苦,仍是笑得真诚,“枫眠幸甚,还望公公上达天听。”
“自然,自然。”浸淫深宫多年,景安演老泪纵横比起陆从宜也不遑多让。
江景顺着他胡扯了一气,待他接了赏沾了喜气走了,这才去书房中见陆从宜。
他早知道是封平津侯的旨意,称了病说是下不了床,他这样说祁镇翊也没有办法,非但无可考究,还得找太医来照料他的身体。
“平津侯?”陆从宜冷笑,嘴里还没往祁镇翊身上甩刀子,先骂起王宽是个乱臣贼子。
江景已经听景安提过那位王大人了,他是皇上提拔的寒门,同世家打擂的,如今做的是户部尚书的位子,很有一番权势油水,在皇帝面前想必也有一定分量。
毕竟今日皇上下旨,御书房里待得就是这位王大人。
“当日翟将军何等气势逼人,长公主何等骄矜恣意。先帝早有示下,要为你改姓封王,那时谁敢说个不字?你朝见那日,分明是叫皇帝钻了空子清了场,朝上站着的要么是他的人,要么是一干墙头草,没甚主见惯会附和的。”
他气得咳了声,又接着道:“纵然他不愿遵先帝的意思替你改姓封王,若当真疼惜你流落在外,也大可给你个沉阳侯的名号,府邸财物事小,平津却是哪朝哪代的旧例?”
陆从宜话里话外都很有替他委屈的意思,江景听出来了,惊骇非常,饶是他也知道沉阳侯的名号绝不能轻易封给谁,更何况他生在沉阳,若真给了这样一个名号,岂不是放他与沉阳江家牵扯纠缠,皇帝如何能容得下这样的局面?
其实在京中诸人眼中,皇帝对江景这个半路冒出来的表弟已然算是荣宠,毕竟这些年翟家对翟措的影响模棱两可,先帝的意思又不为众人所知,然而江景总觉得陆从宜在他的身份上有种超乎寻常的执着,这种执着,绝非仅仅因为同江景亲生父母的关系,他不动声色的掩去眸中思量。
他自然没敢像陆从宜一样去置喙天子恩赐,只是委婉道:“我是翟家的后人,翟家毕竟是罪臣之族,或许皇上已然开恩。”
陆从宜听了这话更气,咬牙切齿,“你知道什么?翟家,翟家……”
陆从宜么没再往下说了,“封侯事多,你且回去,日后还有的忙。”
江景知道他有未尽之言不肯再说,虽心下焦灼,到底也没再逼问,只是告退不提。
为什么?翟家人受了那样的刑罚,分明是获了大罪,即便他父亲彼时已逝,总不至于叫皇帝对他毫无芥蒂,翟家的事为什么影响不了翟措,为什么不该影响他?
江景长到二十有二不曾在皇家待过一日,他对这道封侯的的旨意并无不满,只有满心猜忌,还有隐隐的讽刺。随霍大帅来京时他曾暗示要上折子为江景请一个将军的位子,让他去南疆守着,彼时江景也知道自己因着江莫两家的牵扯很难得用,即使大悦缺良将之才,即使百姓遭铁骑欺凌,果不其然,霍南闵向他透露折子被皇上搁置迟迟没有定夺,其实也在意料之中,毕竟若非情势所迫,他也不觉得自己的军功能够得上像霍大帅一般独当一面的位子。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从前总觉得封候拜相在乱世总归染着血,后来才发觉这条路也能走的花团锦簇,原来但凡扯着皇家血脉,便是天定的尊贵,不必骨血铺路,也能尊耀人前。
祁家的血竟这般贵,纵使三军九城也抵挡不过。
皇上肯为他封侯,大底也存了日后叫他重返战场的心思,江湖之人难用,再添一层祁家的血脉就会显得更得用吗?这样也好,恰正合他的心意。
江景默然,只不过在这之前他还得做些旁的事。
“主子。”
身着黑衣的身影悄然跪在他身前。
江景不自觉揉了揉眉心,“如何了?”
“家里没什么动静,江、莫两位家主都还镇得住,只是新近有一批人联系上了我们,对方声称自己是……大长公主为主子留下的人。”
江吟一向稳重,报出这样的消息也显得犹疑不定。
江景狠狠攥了攥手,心里咯噔一下。
“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身份,这些年又做过什么事,如何找上你们的,可一一查清楚了?”
眼下时局混乱,有什么人冒充大长公主的人引他上钩也未可知,若真是这样也好,若不是,那么大长公主是否也早料到他身份被揭穿的今日,她与陆从宜没说出口的目的是否一致?假如江景不曾上战场,不曾随霍南闵入京,他们又当安排怎样的计划来揭露他的身份?而大长公主若想他回京,起初又何必将他寄养江湖?她选江莫两家是偶然还是深思熟虑?她为他留下这些人……是打算做什么?
“这些人的身份都杂乱得很,从朝廷命官到江湖侠士,牵头人递了一份名单,但不肯暴露自己的身份,说是想见您一面。”
“查不出来?”江景有些惊讶,江吟等是爹娘留给他的人,他一向信任他们的能力。
“属下无能。”江吟惭愧道。
“无碍。”江景沉吟着接过名单,目光扫过那些或在庙堂或在江湖的名字,接连确认了两遍,没有陆从宜,也没有徐楠,他喃喃道:“这一局,可真是玩大了。”
青年脸上难得恍惚,他看着江吟,“我原想自己心在江湖,无意江家之势,武功亦不负爹娘无双之名,要你们来跟着我做什么?”
他合上那份名单,“你说我爹娘是不是也早料到今天了。”
江景尚年幼时,江岸同莫君涵就为他挑了七个孩子,冠上江家的姓,或习武功,或精毒术,或通岐黄,或掌查探,日后送到江景身边去守着他,告诫他们誓死护卫他的性命。
他们都是身世可怜的孩子,若非当时,也无今日,江吟沉默不语,自从被冠上江姓,就以江景马首是瞻,无论主子前路如何,唯拼死护主而已。
江吟嘴笨,向来说不出什么肉麻的话,江景知道他的忠心,也不像江诵那样时常逗他,偏要将他逼得面红耳赤才肯罢休。
江诵是江吟的亲弟弟,也在七卫之列。
他转了话头,“多日不见江诵了,我要他查一查旧案,就这般难,让他不敢回来复命了不成?还是说醉在哪处温柔乡不肯起了?”
江吟听着想起江诵一向寻花问柳的做派,脸都黑了,他朝江景行礼道:“江诵顽劣,主子恕罪。”
“不,他很聪明。”江景挑眉道:“不想他去青楼?”
江吟冷道:“浪荡小人做派。”
江吟比其余六人都要大些,幼时也总把他们当弟弟照看,对江诵也是悉心照顾,哪里想到他日后长成这般。江吟为人正直古板,又唯江景之命是从,自然愈来愈看不上江诵那个自作主张的不守规矩的样子。
江景管不来他们的事,只想着要见他的那个所谓牵头人,
“跟那人说,明日午时,明湖楼上,恭候大驾。”
江吟正想应是,却听得房顶的动静,他警觉道:“谁?”
“刚才还念着,是江诵回来了。”江景笑道。
果不其然,正是江诵进了房门,一身花花公子的穿戴,浑身的脂粉气还未散,他先朝江景行了礼,“主子。”
又转身朝江吟笑得讨好:“头儿。”
江吟冷哼一声。
江诵摸了摸鼻子,他来时正听见了江景的话,不由劝道:“少主现下封了侯,正是打眼的时候,不若过两日分了府,再叫人到府上见,明湖楼总归太惹眼了些。”
江景高深莫测的摇摇头,“我这时去酒楼见个江湖朋友算什么,只怕日后领到府上见才更叫人生疑呢。”
江吟原想教训江诵不该质疑主子,现也顾不上了,听见江景的话,两个人如出一辙的惊骇,江湖朋友?
怎么可能是个江湖人?
大长公主留下的那一串名单,位高权重者大有人在,这些人会甘愿叫一个江湖人牵头?
江景看出他们两个的惊讶,难得见他们一致的时候,不由起了逗弄之心,含笑道:“且去回了那人便是。”
“是。”不等江诵还要再问,江吟应着是,便把人拉了下去。
江诵受他桎梏,难受的很,出了门便反抓住他的手腕,“头儿,难道你就一点不好奇?”
“好奇什么?做好你的事,听主子令就是了。”江吟挣开他的手,问他:“你去什么地方鬼混了?”
江诵闻言做了个委屈的表情:“冤枉啊,头儿,你知道我是奉少主命去探翟家旧案,翟家人要么流放去苦寒之地,要么流落秦楼楚馆,我一时去不了边疆,若再不肯去青楼,怎么探?”
江银知道他的花花肠子,半点不受他蒙骗,“翟家人都算是同主子有些关系,你莫要乱来,别误了主子的事。”
“头儿,放心吧!我知道的。”
“你最好是。”江吟看着他嬉皮笑脸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自顾自递消息去了。
明湖楼,四下寂静,苏祈玉替徐衍倒了茶,
“行之,你这两日是怎么了?国子监也不去了,见天地往陆阁老府上跑。”
说着,他装摸做样的叹息:“可怜咱们先生一心想教出个状元,怎奈这状元苗子看不上国子监的先生来教呢!”
徐衍冷着脸,“胡说些什么。”
“哪里是胡说?你去阁老那里难道不是讨教学问?”他慢悠悠的饮了一口茶,笑道:“有陆阁老来教你,不怕教不出个状元来。”
徐衍瞧着他,“不是讨教学问。”
苏祈玉不相信,“不是讨教学问还能是什么,难不成是去见那位惊才绝艳的长公子?”
徐衍提醒他,“昨日圣上下了旨,如今应当称平津侯了。”
苏祈玉不以为意,“无论如何,你文人气质太盛,性子又冷,怕是与长公子相处不来。”
抱着长公子不舍得撒手的性子冷的徐衍听着苏祈玉的话,知道这些时日里京城没少传江景的事,“你又听得他什么消息了?”
苏祈玉是京城公子哥儿里出了名的爱打听,收罗着四方秘闻轶事,但他这会听的不是什么侍郎小姐同落魄书生私奔,世家公子为花魁赎身的消息,他脸上难得带点敬畏又憧憬的神情,“听说侯爷十五上战场,那时他尚未入军营,算不得将士,不曾穿军甲,只是一袭寻常白衣,踏马持刀,如入无人之境,刀锋所过之处,白衣染血,似落红梅。”
苏祈玉说着,眼神怔怔的,“何等的风华!”
徐衍的眼神却仍是淡淡的,“战场厮杀,竟也叫人传成这样风雅的样子。”
他想,若江景在战场上真能这样游刃有余也好,他这些年就不必日日提心吊胆,不必为他辗转难眠。
苏祈玉这时回神,笑道:“那有什么,当日麒麟街上咱们也不是没见过侯爷,一众将军里,最打眼的就是他,那般人物在何处风雅不起来?”
人性爱美,美人总能叫人赏心悦目,徐行之生的这样一副得天独厚,宛若谪仙的容貌,眉眼似冰若雪,身姿恰若翠松劲竹,惹得多少姑娘等着他。苏祈玉想着,江景来了京城,便不会有那么多姑娘愿意等他了。
徐衍不愿意听旁人谈论江景的容貌,三两句将苏祈玉的话题扯开。
以至于苏祈玉早忘了初衷,又要兴致勃勃地同徐衍说他那些野路子来的消息,
“你可还记得霍大帅回京那日,我同你说戚家的小姐也在。你猜猜,她来做什么的?”
徐衍自然记得那位戚小姐,戚若,戚阁老幺女,自幼体弱,养在深闺,少在人前,与宁国公世子程原宿有婚约,麒麟街上盯着霍钦的人。
他心下一动,不答反问,“她来做什么的?”
难得见徐衍对这些事情感兴趣,苏祈玉忍不住卖弄,“戚小姐同程世子定有婚约原是宁国公府老夫人的意思,程世子心高气傲着呢,看不上弱柳扶风的病美人,嫌弃人家是个病秧子。”
“他是这样说的?”
“当然不是,他哪里敢,他若敢如此,即便戚阁老不做什么,宁国公也不会轻饶了他。谁不知道戚家心疼这个小女儿,眼珠子似的护着。”
苏祈玉好笑道:“程世子这人真有意思,他反不了这门亲事,一没发怒宣泄,二没借酒消愁,只是去戏楼时大肆夸赞霍少将军。”
“说来听听。”徐衍侧目。
霍钦在京城百姓之中也很有声望,女子为将,历来艰辛,戏楼中有些关于她的戏目也不足为奇。
“能有什么,不过说霍少将军是世间奇女子,女子如此方是世间真绝色那一套。原也没有什么,但是戚若同霍钦两个人就像是这世间最不相似的女子,谁听不出来他是对婚约心有不满呢?”
他倒聪明,不明说,戚家也不会上赶着认为女婿对他家千金不满。徐衍想,宁国公府同霍家也算沾亲带故,上一辈的霍家女嫁到宁国公府,所以程原宿算来应当是霍钦的表弟,又正值霍大帅即将回京,他当众夸赞霍钦总归合情合理。
“戚家小姐玲珑心思,听了未婚夫这样的话哪里有不明白的,怕是要来亲眼见见霍少将军英姿的。”
是这样吗?徐衍回想麒麟街上戚若看霍钦的眼神,有些熟悉,他曾经也见过那样的眼神吗?他怎么也回想不起来。
是他当日太在意江景了,心神都拴在那一个人身上,徐衍喟叹。
他放下茶盏,偏头往窗外看去,这随意一瞥正瞧见那个让他心心念念的人。
“不喝了,换个地方。”
“啊?什么?”苏祈玉一头雾水地跟着徐衍出了明湖楼。
江景是来同他那位江湖朋友赴明湖楼之约的。
他封侯的消息人尽皆知,行踪多有顾忌,这个时候能在京中天子脚下不递拜帖而私下见他的,定然不是个庙堂中人。
眉眼昳丽的青年吸引了不少目光,江景来到约好的雅间,里头已然有人在等着他了,此人身着青衫,背对着他,江景心下狐疑,仍旧收拾好心情,谨慎道:“阁下……”
那人却在此时转过身来,是个青衫白面的公子,手里拿着一把半开半合的竹骨扇,言语里带着熟稔和笑意,“多年不见,枫眠,你见了我,可还欢喜?”
江景余下未尽之言都被吞到肚里了,他此时震惊疑惑大于重逢之喜。
“许放?”
“嗯哼,是我。”
许放是沉阳忘忧山庄的七公子,他们家同江家往来颇多,江景与他自幼相识,上次见面还是江景参军四年后在北境锦州,那时许放办事途经锦州,多年不见也欢喜得很。
“你亦早知我身世?”江景问得咬牙切齿,无他,江、莫两位家主,陆从宜、徐楠,这也罢了,毕竟都是长辈,现今又多了个许放,好像就只有他这么一个当事人被蒙在鼓里似的,“怎么会,连你也知道。”
“不,你别误会,我不知道。”许放看他那气急败坏,上来就要给他一掌的样子,大笑几声,连连后退,摆手道:“枫眠,我也是直到麒麟街上陆从宜当众揭露你的身份,才知道的。”
江景看许放不像是骗他的样子,又想他大抵也还没有那么神通广大,他平了平心气,“这事儿的来龙去脉,你最好是能给我解释清楚。”
许放为江景倒了茶,言简意赅,“我十五那年,有幸见了大长公主,她问我是否想做一件大事,将一份名单交付于我,嘱咐了我诸多事宜。”
许放十五,便是江景十三的时候,他想,这个时间距爹娘战死,翟家获罪,大长公主薨逝还有两年的距离,倘若如此,大长公主为什么要在此时留后手,又为什么要选许放这个当时尚年少的江湖子弟来做日后的牵头人?
不,等等,江景狐疑道:“你十五的时候,来过京城?”
许放摇头,“并未。我见大长公主,是在沉阳。”
许放知道江景心中定然有诸多疑惑,当时他心中惊涛骇浪不比江景少半分,居然是江景,江家同忘忧山庄同在沉阳,他查了那么多年都没半点踪迹的人,居然与他相隔如此之近。
许放虽然是无忧山庄的公子,但他同庄主的关系并不好,庄主好色多情,许放的母亲不过一介舞女,怀了许放后便不再得宠,庄主的孩子很多,并不很在乎骨血,许放的母亲既是那般出身,母子二人没甚地位,日子过得艰苦,后来母亲更是被磋磨至死,许放因此自幼饱尝世间冷暖,只不过武功尚佳,又兼才智,即便是在一众兄弟姐妹中也能显得出色,这才被家族重视。
“你可知道武林第一高手燕无痕同当年葬花宫主余瑾年的沉阳之约?”
燕无痕,武林第一高手,江岸少年时曾有幸得他教诲,一手踏雪无痕的轻功超绝于世,手中使的是双刀,一名乾,一名坤,两刀一亡魂。
葬花宫主余瑾年,内力深厚,不借刀剑兵器,以花为锋,叶为刃。
燕无痕同余瑾年师出同门,两人私下有一番恩怨,约定某年某日于沉阳绝顶峰一战。
原本不过是两个人的生死恩仇,后来竟演变成整个江湖的大事。
江景自然清楚,“燕无痕同余瑾年那一场沉阳之约本该是江湖百年来最接近统一的时候。”
那时燕无痕还没被冠以武林第一高手的称号,他同余瑾年平分秋色,江湖中老一辈都等着这一场决战分出胜负,推举出一个能以武功服众的武林盟主来。
有人看重燕无痕剑承正宗,豪侠仗义无牵挂绊身,当得起日后公正无私之举,有人称余瑾年背靠葬花宫,又内力超绝,当比燕无痕更易得人心。然而这些猜测后来都未落到实处,从前不管站了谁的队的都没能得到什么实际回报。
没有人做了武林盟主。
绝顶峰上当世顶尖高手对战,剑出染血,花叶伤人,草木皆惧,生人勿近。
九年前那场沉阳之约至今仍是难解,从绝顶峰上下来的明明只有一个燕无痕,可他偏说自己没赢,推了这唾手可得的武林盟主之位,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如今江湖势力林立,武林离心比当时不知严重了多少倍,早已不见当年盛况了。”
许放这声感叹惋惜的亦真亦假,江景知道重点不在这里,被燕无痕和余瑾年作践行沉阳之约一用的绝顶峰本是忘忧山庄的地界。
“你说你并未来过京城,又提起绝顶峰一事,难不成你同她是在绝顶峰得见?”
这话问得江景自己都惊异,世人皆知当日绝顶峰上唯有两大高手决战,而余瑾年命丧于此,最后走下来的不过后来被认作第一高手的燕无痕一人。
假如除这两人之外还有人在绝顶峰,那么他们是何目的?围观高手决战讨教以求武功精进吗?
“是,当日,大长公主,我,都在绝顶峰。”出乎意料,许放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江景心想,要练就这样一身不动声色的本事其实也不是非常费力,古人说熟能生巧,诚不欺我,他实在再做不出什么惊异的神情了。
因此他只是缓缓替许放把空了的茶盏又添满,叫许放一点也看不出他的心慌来。
“枫眠,你是真的,长进了。”
他们两个都心知肚明,许放今日绝不是来同老朋友叙旧的,他是来瞧瞧当日那人以某种许诺换他一世效忠的主子,看这人是否值得他倾尽此后心力。
江景从来都知道许放处境艰难,他十五的时候哪里顾及得上什么绝世高手绝顶峰对决,那时他生母早逝,江景也去了京城,他总是一众兄弟姐妹的欺凌对象,每日里想得不过是怎么能叫自己日子再好过些。
江湖世家子弟对高手对决心生向往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奈何刀剑无眼怕伤人命,峰顶地窄也不甚可观,两位高手又明言不愿叫人围观,这才使得人有贼心没贼胆。
但绝顶峰毕竟是无忧山庄地界,若庄中有人想看也并非绝无可能。
“他们逼你去绝顶峰了?”江景压着火气问。
他话中的他们指的是少时常常欺压许放的一众兄长。
许放一愣,蓦地想起少时江景在无忧山庄撞上他被四哥许劲欺凌,那时少年意气,持刀出鞘,手松松按在刀柄上,不过须臾,刀刃就逼近许劲眉间了。
江景比许劲整整小了五岁,那时少年眉眼纤长,容色隐隐还有些姑娘的样子,却丝毫无损他英气,也能窥出几分日后的潇洒风流来,他说的什么来着,许放回想,“无忧山庄四公子,领教了。”
那应当是许放平时难见的许劲挂不住脸色青白又发红的时候,但他其实记不得他四哥的表情了,丝毫也记不得,只记得白衣墨发的少年张扬恣意持刀入鞘的模样。
“没有,他们哪有这么无聊。”许放轻轻笑着,“他们叫我去采苍云耳。”他的声音越来越轻,“是我自己迷路了。”
江景听了这苍云耳火气没收敛半分,这苍云耳是沉阳峰林之间独有的药材,药是好药,只不过因为这种药材有异香,总能吸引一种猛兽,这种猛兽便被称作苍云兽,是以苍云耳高价难求,采药人若武功平平便是九死一生。
忘忧山庄也颇受江湖尊敬,但江景瞧不上庄主叫一堆继承候选人你死我活的做派,江湖名门子弟不悉心钻研武功,半点不顾手足情谊与江湖道义,没得辱没了家世门楣。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许放没打算同江景诉苦,“当日我阴差阳错上了绝顶峰,见着两位高手时,他们战况正酣,只恨我当时武功低微,并不足以领悟一招半式,他们全力对战,没有多的心思分给我,我又惊又惧,虽不敢近前,一时却也不知中了什么迷魂药似的半点不想走,于是只远远躲在一边看着。”
江景没想到许放曾离那场江湖闻名的决战如此之近,他预感今日就将知道九年前绝顶峰一战之谜,只听得许放接着道:“燕无痕同余瑾年平分秋色,一时分不出高下,但此时两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有些伤,然后……然后上山的小路上突然杀出了一批蒙面人。”
许放讲到这里,闭了闭眼,他当时年少见识浅,遇到这种情况慌了神,加之又离得远,是以根本记不清那些人身形特征,更莫说姓甚名谁。
但他们都知道,敢在这个时候冲出来的,必然都不是无名之辈。
江景听到这里已然明白他的意思,“他们是来帮我师祖的,还是来帮余瑾年的?”
“这一批,是来帮余瑾年的。”许放的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嘲讽。
江景从他的“这一批”琢磨出些别样滋味来。
这也是必然的事情,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燕无痕同余瑾年的私人恩怨一旦牵扯上武林盟主的位子就不会只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这当中牵扯着多少世家、门派的利益与武林格局,又有多少人愿意为此放手一搏?
“这批人一出现就直接对燕无痕动手,原本的两大高手对决变成一场卑鄙的围攻,他们的武功都属高手行列,燕无痕再怎么厉害也禁不住一众高手同时动手。”
当时许放也以为他们是余瑾年的人,也以为是葬花宫主欺世盗名,唯恐敌不过燕无痕,罔顾江湖道义,要用这样的手段来得到武林盟主的地位,热血少年的世界里非善即恶,非白即黑,他为燕无痕揪心,希望这位名满江湖的大侠能绝处逢生。
“可是我错了,我觉得或许江湖传言有误,燕无痕同余瑾年根本没有什么仇怨,不过是两个绝顶武痴要探一探彼此的武道而已。”而现在许放对江景如是说。
当时燕无痕被围攻之下受了伤,而余瑾年,他见众人围攻,不惊不怒,朗声道:“燕兄,我们的对决虽被打断,但你我招式已在我脑中演化数遍,每一遍,我都是必输的结局。”
他这番做派在当时那种情境分外奇怪,以至于众人一时停手。
“师兄,你我决战到此为止。”他扫视众人,“既有人拦路,怎么也不会尽兴。”
他轻功超绝,朝燕无痕的方向去,快的叫人看不清身形。
蒙面人以为他要动手了解燕无痕。
“连累你受伤真是过意不去,就拿我的血来祭你的剑吧!”
电光石火之间,余瑾年夺了燕无痕的乾刀自刎,容颜染血,一跃下高峰,以死为这场沉阳绝顶峰之约画上句号。
余瑾年既死,蒙面人无比吃惊,他们想不通为何大局将定,余瑾年却要抛下唾手可得的胜利,但他们不约而同的没再对燕无痕动手,他们作了装扮又谨慎的没用自家武功,不怕被燕无痕认出来,此是不必;绝顶峰一战两大高手皆陨落定然因蹊跷多生事端,此是不敢。因此这些人都从来时的小路迅速撤了回去。
燕无痕没去追那些人,他没有将剑收归入鞘,就抱着那把染血的刀,在峰顶站了许久,嘴唇微动,好像说了什么似的。
“哟,这还有条漏网之鱼呢!小家伙儿,你在这里干什么?”
少年许放一直盯着燕无痕的方向,没发觉什么时候自己身边竟站了这样一个人,只见眼前这位女侠容色极盛,脸上带着戏谑的表情。
许放紧张极了,结巴道:“不是,我,不,不是,漏网之鱼。”
燕无痕这时朝这个方向看过来,对这女侠道:“你莫伤他。”
这女侠,就是祁姝华,就是当时的长公主,后来的大长公主,她原也没有要伤他的意思,燕无痕定然知道许放的存在,不过是个好奇观战的孩子。
“我原是来帮你的,我来晚了。”她说。
“你知道有人会来帮余瑾年?”燕无痕问她。
“不,我不知道,我只是来帮你的。”祁姝华坦然道。
燕无痕听明白了她的意思,他皱着眉,有些难掩的厌恶,“既然如此,那你就同围攻我的那些人并无区别。”
“是没有什么区别。”她闻言半点不生气,“早知如此,我便不来了。”
“但我既然来了,总不能就这样回去。”
她的眼神再度转回到许放身上,“无忧山庄的小孩儿,你不错,跟我来吧,我有事找你。”
少年许放就这样一头雾水的被带走了。
祁姝华不伤人命,燕无痕不打算管她做什么,他最终还是缓缓将他的双刀收归入鞘,下山去了。
山下早有人待决战结果,看到下来的人是燕无痕,有人欢喜有人忧,不待众人恭贺,燕无痕先开口,“我没赢。”
他运着一身出神入化的轻功走得决然又洒脱,此后数年都没有人能找到他的踪迹,追上他的脚步。
“你被大长公主带走了?”江景对祁姝华很难有什么别的称呼,他想,总归故去十余年,或许他们也并不很在乎。
“是。”
许放被祁姝华带下了绝顶峰,到了她的落脚处。
“小孩儿,听说你在家中过得不甚好,嗯,你想不想做一番大事业?”
许放当时十五,不该再被称作小孩儿了,但他过得确实不好,长得也瘦弱,身形比不上同龄人,总是显得年岁更小些。
“做了大事业,就能吃饱饭,练好武功,做人上之人了吗?”
“那是自然。”
再回头看的时候许放就很容易知道祁姝华其实早就知晓他的身份处境,包括他的出身,抱负,还有和江景的关系。
但当时他不知道,当年的许放就是这样容易放下戒心,就这样轻易的被大长公主带上一条或上云巅,或沦尘土的路。
“我帮你成一番事业,可是有条件的。”
“好,我答应你。”
或许是因为燕无痕吧,燕大侠认得这位女侠,她可以信任。
江景只静默听着许放追忆往事,隐隐也能明白几分祁姝华挑中他的意思。
无论出于何种缘由,朝中确有人能逼得大长公主为她早就远送江湖的儿子再筹谋一番势力,人心易变,利与义都不能长久,且挑一个心性武功都不逊色的江湖少年,待到他能成事之际,若她的儿子成器,年纪相仿,总不会压制不住他。
既然如此,何必要兜这么大一个圈子送他走呢?江景想。
“条件就是让你日后帮她的儿子做事吗?”江景问的自然,一点也没有自己就是“她的儿子”的自觉性。
“不是。”许放却笑着摇头,“确切地说,不完全是。”
大长公主给他的条件是,假若有一天他认得了她的儿子,就让他奉他为主,护他周全,听他号令。
“好,我答应。”
“小孩儿,你可想清楚了?我说的是任何号令,就算他要你弑君,你也得去。”祁姝华没想到许放答应的这样快,忍不住恐吓道。
江湖的儿女不畏帝王气运,达官贵人的脖颈沾了刀剑,流的不过也是与常人无异的,一样颜色的血。
“那你的儿子他可会叫我违背江湖道义?”
“我的儿子心性必然随我,怎么会?”祁姝华瞪大了眼睛。
“那我就答应你。”少年许放扯着这位女侠的衣衫,“我要怎样找到你儿子?”
祁姝华笑了,“不用找。”
“不找怎么会认得?”许放疑惑。
“等到有一天不必你特意找也认得了他,你就去见他,去帮他;若你一直不认得他,那他想必是在山水间痛快了,自然也无需你帮他。”祁姝华脸上浮现出艳羡向往的神色。
许放不解其意,这些年却一直牢记于心。
大长公主无意叫他牵扯京都,江景确定了这样一件事,心中还有未解之处,却不好在许放面前透露。
他细数这些年声名鹊起的江湖势力,暗自忖度其中对得上许放年纪的,“你是天机楼的楼主?”
天机楼,擅机巧情报,但凡有人出得起价格,便没有买不到的消息。
“不是。你才是天机楼的楼主。”
许放起身,衣袖拂过椅背,“天机楼是你母亲的东西,我不过代为保管而已。”
他说着,又隔空抛给他一个小巧的木盒,“喏,不便借他人之手交予你的,都在这里了。”
江景接着,将东西拿在手里。
许放给了东西就离开了,他从明湖楼出来的时候,随意望了眼四周,只见不远处别家茶楼临窗坐着的两位公子格外醒目,恰巧是他能瞧全的绝佳位置,其中一个气质容貌都极出挑。
他虽惊艳了一瞬,却想着又是京城哪家金贵的人物,没甚在意地径直离开了。
这两位公子,正是徐衍和苏祈玉。
苏祈玉先前还在抱怨徐衍拉他出了明湖楼,“还以为你有什么旁的事,不过就是换了家茶楼喝茶嘛!明湖楼的掌柜招你了?”
只不过苏祈玉向来看不穿眼前这人心思,只以为明湖楼今日的茶招了少爷厌烦,调侃过也就不甚在意。
谈了约有一时两刻,徐衍见着许放出来,记了他的身形样貌。
他放下茶盏,“不说了,走吧!”
苏祈玉起身往窗外探视,恰巧看见从明湖楼中慢一步出来的江景,“行之,你瞧。那是不是平津侯?他怎么在这儿?”
徐衍的视线跟着过去,“是,想必是来会友的。”
苏祈玉点头,“今日有缘,碰上可要一见?”
他跃跃欲试,只等徐衍点头就要下去找这位美人侯爷。
江景没看见他们,徐衍看他不像是要往徐府走得样子,淡淡拉住了苏祈玉,“他过些时日就要入府了。你若有心,就正经递了拜帖去见他,街头茶馆,也是你头次见侯爷的地方吗?”
“那倒也是。”苏祈玉让徐衍拉住,息了去见江景的心思。
江景握着手中的木盒子,隐隐觉得这其中会有什么能解他当下之疑的东西。
他思忖着,一路绕到了望舒楼后,挑了个无人注意的角落,飞身翻了进去。
望舒楼惯是男子寻欢作乐的地方,但也并非就全然没有规矩讲究。打第三层楼往上数的姑娘们便与底下不同了,她们多是清倌艺伎,不肯轻易接客的,平日里只是弹琴唱曲尚需隔着一层帘子,若要见面便是另外的价钱,若男子认定了人,铁了心要求春风一度,这便不止要有足够的银钱,还得合了姑娘眼缘,等着姑娘点头,否则就算是金山银山也不见得肯呢。
“姑娘,姑娘你既不肯见那蒋家公子,咱们不见就是了,何必怄气,难道我还会违了姑娘的意思?”三楼上,老鸨陪着笑脸安慰一个容貌清丽气质出尘的女子,心里却暗骂她不识好歹,想这蒋晟蒋公子也是的身家也是京城里数的着的,她一个风尘女子,说好听些是个清倌,其实不过是个官妓,难不成还以为自己是个官家小姐要相看姑爷,挑挑拣拣的不成?
“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又有什么用呢?我不愿见他,妈妈还不是巴巴收了人家的礼,欢欢喜喜将我送出去?”女子听了老鸨的话也不领情,冷冷反问她,又牙尖嘴利道:“知道妈妈拿我做摇钱树,我也不曾替妈妈少赚了谁的银子,今儿个就叫我歇歇吧!”说着,就拐进了房,将房门一把摔上。
门外的老鸨被气了个仰倒,“给脸不要脸的小贱蹄子!”她一面愤愤骂着,一面忙不迭地去寻那蒋家少爷,收了人家的银子,却没让人家见着想见的人,这事还得好生说道说道。
下了楼,出了门,隔开了楼里的娇声软语,蒋晟就站在后园的凉亭,看着走过来的老鸨身后空无一人,失望道:“怎么,是清若姑娘不愿意见我吗?”
老鸨陪着笑脸,“哪能呢?蒋公子莫要胡思乱想,不过是清若今日弹琴累着了,已歇下了。我想着蒋公子定然不愿意累着她的身子,若是知道了也只有劝她休息的,便没有叫她,蒋公子不会怪罪吧?”
老鸨浸淫风月场多年,看人很有一套,不知见过了多少似这般文人才子痴情妓子的,很是能拿捏他们的心思。
蒋晟闻言,只道:“自然,就请清若姑娘歇歇吧,蒋某明日再来。”说着转身走了。
只剩老鸨盯着他的背影瞧,硬是想破了脑袋也想不明白清若到底是怎么想的,纵然才子痴情不长久,但妓子哪有在乎这个的。
她紧紧握着手中的银票,要说在乎的,还得是这个。
“姑娘,你还要在这楼里讨生计,何必惹了妈妈不快?况且蒋公子言行端正,也不甚无礼,怎么就惹了您厌恶呢?”房里清若身边的小丫鬟忧虑道。
清若面色不改,“我同她有什么?我的琴能弹一日,她就要捧我一日,待到我弹不了的那一日,无论我对她如何和颜悦色,她也不见得会怜悯我分毫,既然如此,我何必要看她的脸色?”
“那蒋公子……”
小丫鬟的话还没说完,清若往窗边看了一眼,打断了她,“茶凉了,你去替我换壶热茶来。”
小丫鬟闻言便不再接着说,应声出去了。
她房里的窗与别人的不同,窗框比寻常的更高更大,用的是上好的金丝楠,倒是窗比人还要金贵许多,这楠木,还是当年从翟家带出来的。
这时她瞧着江景从窗外翻进来,他没落地,就那样松松垮垮的坐在窗框上,摇摇欲坠,很有几分美感,她的眼神终于有几分波动。
“你下来,莫要压坏了我的金丝楠。”
江景这才从窗上跳下来。
“你又来做什么?”清若在桌边坐下,桌上杯里有她惯留的茶,这茶自然是凉的,但她却像毫无所觉似的,同热茶一般用着。
“凉茶伤身。”江景忍不住劝道。
“我知道,偶尔一用罢了。”清若不以为意道。
“阿姊,我……”江景在窗外也听见了小丫鬟的话,知道她过得艰难。
清若是翟家姑娘,算来该是江景的堂姐,江景实在是难以想象,一个自幼被娇生惯养,教以诗书的大家闺秀,官家千金,要如何生生折了傲骨,在这样的胭脂堆里委曲求全。
大悦律令,官妓或可买卖,不可赎身,终生不能脱贱籍。
江景叫江诵查了翟家流落在青楼的女眷,过去了七年,期间物换事转,而今便只剩下这一位堂姐,清若第一回见江景时就知道他所来为何,明白告诉他,“翟家人不畏死,却不能死的不明不白。”
她一直在等他来,旁的人都熬不住,她们都死了,她也熬不住,但总还得剩下个人给翟家后人留点消息。
她这样的话一出口曾让江景不禁心悸,这样的人像是将命吊在这最后一口气上似的。
“不会的,既已熬了这些年,总不能白熬,我要看看,二叔究竟犯了怎样的罪?这罪又是否够格要我翟家满门的命来抵。”
现下是江景第二次来,可他这句阿姊一出口,就叫清若变了脸色。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知道的都同你说尽了,叫你不要再来找我,你不只是翟家的子嗣,还是大长公主的儿子,还是皇帝亲封的平津侯,不要叫我阿姊,我受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