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为路锦柏关烻的小说《禁欲将军的竹马侍郎》已完结正火热推荐中,小说禁欲将军的竹马侍郎是一本好看的纯爱小说,由作者林怿昔所著,内容是:路锦柏无论做什么都没关系,关烻会原谅他,会和他一直在一起,只要他好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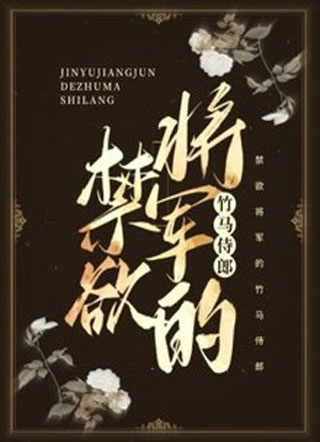
来源:不可能的世界 分类:现代 作者:林怿昔 主角:路锦柏 关烻
关烻回身却不见人影,不禁怀疑起自己,想走到亭中坐下小憩,又听见那声音唤自己名讳。
他忽地跪下行礼,压低声音道:“微臣参见大人。”
到底是在王宫里,关烻不敢把动静弄大,循着声音往深处走去。
这路径和时间选得极为巧妙,趁着羽林军换守躲过耳目,绕到冷宫。
天色深沉,阴森素白的月光直直照在没有树木遮挡的院中,整个院子都散发着寒气。
关烻虽看不清却也知晓,正殿里站着的男人便是自己寻的那人。
男人背对着他,他也不敢贸然上前,于是站在远处问:“大人有何吩咐?”
穿着破衣烂衫仍掩不住贵气的男人将个纸包扔给关烻,“本该不急,只是这药太过奇怪,虽说大军回朝那人不敢显露,但也必定不得安宁。”
关烻抬手接住收好,回话说:“兵符尚在征西将军手中,又有诸位大人坐镇,翻不出什么水花。”
男人沉吟片刻,问道:“你要去南阳?”
“是。”
“南阳可不简单,你能助路大人查案?”
关烻疑惑:“不就是治水和贪官吗?治水已近尾声,那贪官也得别的大人去罚,怎会是查案?”
男人有些意外路锦柏居然没将这样重要的事告诉关烻,“治水官员之死你可知晓?”
“背后缘由不知。”
“路大人便是在查这案子。”
关烻点点头,再回神男人已经不见了。
他踏出宫殿,按照记忆回到宴厅。
回府后,关烻将纸包交给父亲:“这便是王上染恙的源头,大人要我们找出解药,您可认得什么神医?”
关轸捋了捋胡须,“我自会想法子。对了,你请命南下的事王上应允了,大理寺少卿会同去,你切记谨慎行事。”
“孩儿明白。”
防汛工程的图纸是路锦柏设计,监工便由陈勖去做,白日里发现问题,夜里就交给路锦柏去改,如今总算结束,该验收成果了。
可路锦柏昨日寒厥严重晕了过去,今辰又早早起身要亲眼看泄洪。陈勖想到时人多眼杂自己看顾不上,路锦柏有个好歹他回去也不好交差,便让他在驿馆修养。
路锦柏推辞不过,于是纸上写下要点,让阿翔和阿影替他去看。
张正恩在驿馆外等候,没见着路锦柏也不甚在意。
他在路锦柏手底下吃了亏本就不高兴,又听说这几日京城要再派大官来,心中慌乱不知该如何是好。
拜他那不成事的儿子所赐,他纵是有那三寸不烂之舌也无法狡辩。骄奢淫逸事小,克扣赈灾粮和银钱可是要掉脑袋的!偏陈勖和路锦柏也不透露究竟是何人要来,他整日忧心难安,唯恐自己一见着人就被拖走。
水渠修得虽急,但贵在深厚,开闸放水的瞬间,大半本不该留存的水汹涌地顺着河道而行,直通城外,喧嚣水声震耳欲聋。
陈勖看得心惊,有些佩服路锦柏。
他先前还不明白,直接连通并不影响官道和用水,为何大费周章再接几处本就合适的支流,将大湖水也往下引,现在看来路锦柏是真为南阳考虑。湖面多是静水,城外的百姓可行渔业。干支流水量大,河道宽而深,又与多地的河流交汇,最适宜通航。
如此以来,不仅解决了南阳上下的水患,航运也能发展起来。
岸上的众人无不佩服,全都静默着看这盛大景象。
路锦柏留下不单是休息,更是观察驿馆斜角处的当铺。
按照他和阿翔打探到的消息,今日那东家就要来查账。他注意问了附近的居民,把大概路线图画出来,确定他每次来都会去城中酒楼定个包厢。
路锦柏换了简便的粗布衣裳走进酒楼,特意寻了个能清楚看见门口的角落坐下。
店小二对着他上下打量,末了显出个笑脸来,尽责地介绍道:“客官是要吃些什么?咱们这儿烧鸡和酱鸭可是一绝,配上壶桃花酿简直赛神仙呐!”
路锦柏粗布衣不是白费的,点了两道青菜就满脸可惜说够了。店小二见捞不到油水转身就去后厨。
一坐就是半日,午间阿影和阿翔来寻他,简单概述工程结果,大力赞扬他是何等聪明才智。
路锦柏无奈摇头,让阿影收敛些,不可引人注意。
“公子,门外那人像是在找咱们。”阿翔出声。
路锦柏抬眼望去,确实有个男人向里张望,他立刻把头低下让阿影记住那人长相。
一来他们势单力薄,二来还未见那异乡人的真容,倘若这是他手底下来探风的人,往后他们便别想查出真相了。
须臾,男人轻快往楼上奔去,径直走向个房门紧闭的包厢。
阿翔不动声色出了酒楼,轻快跃上屋顶去看,路锦柏和阿影则继续等候。
很快,几个服饰超常的人也进来,直直往同一个包厢去。
阿影眼珠子在几人身上转来转去,专注的目光令人生疑,最凶悍那个顿时瞪了过来,吓得他连忙低头装没看见。
等人都看不见了,路锦柏把头抬起来,“都记住了?”
“记住了,回去立马能画。”
“好,回去吧。”路锦柏起身。
阿影不解:“不抓回去?”
路锦柏有些好笑:“你我加上阿翔三人能把他们都带走?即便是能,你又能问出什么?都是底下的人,手里没什么消息,咱们还得顺藤摸瓜。”
“是。”阿影失落答。
留下阿翔继续蹲守,二人去找洛淮。
洛淮刚从灾民那儿回来,见到路锦柏十分震惊,结结巴巴问:“大人怎么这副模样……”
路锦柏徐步坐下,将昨日的情况说与洛淮。
“大人这些日子都有喝药吗?”洛淮边问边给路锦柏搭脉。
“每日都按你所说照做。”
洛淮两只手腕都把了脉,“大人四肢逆寒可有转变?”
“手脚更觉寒凉了,是方子不对吗?”
洛淮摇头,“这是开始起效了,过些日子到了极致便会回温,大人禁不住寒,可每日服用姜汤,夜里泡脚驱寒。”
路锦柏了然,一番言谢,留下一锭银子作为诊费。
“这可使不得,草民受不起。”
阿影劝道:“洛大夫,你是我家大人的大恩人呢,这些都是轻的,只是我家大人这次来没带够银子,你若是不收,我家大人不敢再让你瞧了。”
洛淮直笑,“大人您吉人自有天相,大启有您在不愁国安。”
傍晚,陈勖推了张正恩的晚宴邀约,说城外的水利工程有些问题,让路锦柏同他去看看。
“午间阿影来报一切安好,可是晚些出了什么岔子?”路锦柏担忧,阿影却觉得奇怪。
早晨陈大人还让他家公子休息静养,这会儿却让他了看工程。他知道陈勖是个好官,可就怕这好官突然变坏了,他不放心,又叫上了阿翔。
于是几人各怀心事到了城门口,阿影眼睛是最好使的,第一个发现有几辆马车过来。
“公子,是少将军来了!”
路锦柏茫然无措,没想到陈勖居然还玩儿这出。幸好他回驿馆便换了衣裳,不至于让关烻笑话。
“修竹!”关烻激动的声音传来。
路锦柏还未反应过来,浩浩荡荡一行人已到了跟前。
关烻几乎是从马上飞下来,三两步奔到路锦柏身前。看他着挼蓝衣袍,半束青丝,杏眼薄唇清秀儒雅,像是画里出来的人儿,内心欢喜开口就道:“修竹,我来了。”
路锦柏本还期待着他说什么,这下子被逗得噗嗤直笑。
关烻臊红了脸,无措地挠后脑勺,又转头问候陈勖:“陈大人安好。”
“少将军安好。”
大理寺少卿萧艾珏也掀了帘子出来,简单寒暄几句便要进城。
“且慢,”路锦柏出声,将今日酒楼所见悉数告知,“同时这么多人进城反倒打草惊蛇,咱们分散开来。萧大人先同陈大人安置吧,我和凌风稍后便来,有事明日再议也不迟。”
“也好,那我便先去,张大人那边,你还是不要出面的好。”萧艾珏领了圣谕,要将张正恩革职查办。但张正恩不见棺材不落泪,至今也没将重要档案交给陈勖和路锦柏,不利于他们之后在南阳城办案。
路锦柏应声行礼,目送着几人远去,这才回身看关烻。
时隔一年,关烻锐气不减,剑眉星目意气风发,与他记忆中的少年好似没有不同。
“是你让陈大人瞒着我?”路锦柏挑眉,有几分兴师问罪的意思。
关烻又不好意思了,别扭地转头让剩下的人都就近整顿休息,“我走时要你在城门口迎我,可你来南阳了,我想要你给我补上。”
路锦柏见了关烻后脸上的笑就没再收起来过,“立了功的小将军,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
天色渐沉,风也越来越大,路锦柏的发丝逐渐从身后飞舞飘至眼前,关烻细心为他拢好,想到路锦柏不能受凉,又命徐季去取披风来。
“你说洛大夫有法子治疗你那怪病,可有好转?待会儿我再陪你去看看,早日痊愈也好放心。”
“今日才诊过脉,初见成效,不急。”路锦柏并不贪心,能治好缠绕多年的疾病已是万幸,哪儿还敢求得灵丹妙药保他药到病除呢?
披风拿来,是关烻在京中最爱的一件,衬得他威严冷峻,配得上他少将军的身份,而不是让人瞧不起的小孩儿。
关烻亲自给路锦柏系上,顺势拉过路锦柏的手,发觉冷得跟冰块儿般,不免皱眉,一边握紧一边问:“你不是说已有成效吗,怎么比从前还过,还是说这一年又严重了?”
他常年习武身体温暖,这么握着路锦柏反而不适应,脸都顺带着热红了好在天暗关烻也看不清,“这是要催它发作,发作过便好了。”
关烻点点头,还嫌不够,把人拢在怀里,“那我可得时时在侧护着你,若是你晕倒了我也能立马接住,可别摔坏了。”
“你可别咒我,”路锦柏脸皮薄,阿影和阿翔就在不远处,被人这么看着他不自在,于是挣扎着让关烻松开。
三三两两进了城,关烻和路锦柏走在最后,说些没在信里提到的事儿。
“张大人送你的金锭你真打算收?”
“为何不收?”
关烻不敢相信,路锦柏怀君子之心,怎么会在金钱面前栽倒,“那王上若是治你受贿之罪,你当如何?”
“我可没说要自己留着,”路锦柏认真道:“那些都是张大人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自然得还于百姓身上。”
“把钱分给他们?”
“救急不救穷,我打算先帮他们修缮房屋和良田以保证生存,致富还得靠自己。”
他画工程图时去过洪水淹没的乡村,一来,大部分房屋都还坚固屹立,修葺过便能住人,再来,民间的房子多是祖上流传,与百姓而言有深重意义,能继续住下去,想来他们应当是愿意的。
耕作的种子他已经在考虑,既要适宜当地气候,又要有经济价值,要多看看。
一夜好眠,张正恩被按律定罪,押入大牢等候发落,蒋英被提上来,帮助他们了解本地各种情况。
“昨日阿翔盯了半日,那当铺东家不止是异乡人,他们的言语像是外邦人,这是接头人和外邦人的画像。”
萧艾珏看了又看,从外形来看没有什么差距,“那会是哪里人?南蛮?若是真的,勾结外邦谋害当朝官员,通敌叛国够他诛九族的!”
“会不会是张正恩?他贪图钱财被发现,索性杀人灭口。”关烻摸着下巴问。
陈勖摇头否认:“我已查明,张正恩虽收过当铺送来的银子,也只是讨好他行个方便,并无别的联系。”
“那便是有人借外邦之力铲除异己了。”路锦柏指着接头人的画像,“查出这人是谁,先暗中观察他身边可疑之人,那些外邦人或许还不知咱们如今情形,驿馆内加强部署,诸位大人最好不要出去,若是真有人来,咱们便瓮中捉鳖。”
“若是他们不来呢?”关烻问。
萧艾珏答:“那便继续蛰伏,收集证据。”
路锦柏又派人去找几个懂南蛮语言的,尽快知晓他们究竟在交换些什么情报。
不好出驿馆,路锦柏就在房内看书,世上作物种类繁多,适宜在南阳城生长的作物也不少,可就是找不着经济价值高能作为货物流通的。
“修竹。”关烻推门进来,把鸡汤面放在圆桌上招呼路锦柏快来吃,观察起路锦柏这间房。
路锦柏放下书走过来给关烻倒了杯茶,奇怪道:“你是觉得这驿馆有什么问题?”
“不是,”关烻坐下,接过茶一饮而尽说:“我先看看窗户和房梁,真有人来了我好护着你。”
路锦柏无言,夹起面先喂给关烻,关烻摆手:“特意着人给你做的,快吃吧。”
路锦柏执意喂他吃了一口,戏谑道:“怕你给我下毒。”
关烻囫囵咽下,“修竹,你这般,我……”我愈发扭转不了了!
路锦柏低头吃面,以为他又在为没辨过自己懊恼,又给他倒了杯茶,“好了,不逗你了,你替我看看该让灾民种些什么。”
那杯茶同样杯一饮而尽,关烻不大情愿地坐到案几前。
他很佩服路锦柏常常能对着书坐一整日,他要么坐不住,要么对着书犯困,幼时没少挨母亲打。他那将门出身的母亲,打自己孩子也不留情,要不是修竹拦着,他早被打断了腿和胳膊,那儿有今日功勋。
兵法他还能看看,这讲作物的他只觉枯燥,对照着路锦柏写的参考依据看得头疼,几欲睡去。
“修竹!我找到了!”他忽然大喊,把路锦柏吓了一跳,筷子都差点掉了。
“鹿衔草,喜湿,全年均可收,可治金疮出血,祛风,解毒……我看不错,修竹认为呢?”
路锦柏继续看,“均系野生,于湿润草坡或青杠林内……南阳确实能人为栽种,就是地势不好,要多费心力。”
关烻想到路锦柏刚完成的浩大工程,谄媚道:“人为栽种可提高产量,作为药材也不愁销路,加上路大人的通航大河利于运输,何愁没人愿意呢?”
都是普通百姓,又长于田野,怎么会怕吃苦,有杆子当然要抓着往上走。
“我先记下来,下回洛大夫来我再问问价值如何。”路锦柏挽袖提笔,皓腕白皙,手指骨节分明干净有力。
关烻暗自对比,自己的手要大些,还有舞刀弄枪留的不少茧子,不如路锦柏秀气。
一张椅子两个人挤着不舒服,关烻起身让徐季来收了碗筷,自己坐在圆桌边看另一本书,不过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没多久又开始犯困,几次下来直接趴着睡着了。
路锦柏好似预料到会有这般,走到架子前取下昨日关烻给自己的披风,小心给他披上。
可惜关烻睡得深沉毫无知觉。
路锦柏拿过关烻看的那本书继续看,到眼睛都感觉疼时发现了紫苏。既能药用又能作为食物,散风寒,益脾利肺,寻常百姓家的菜园就能种植。
想好要种什么,路锦柏又开始计算成本。
药材的种子大多也有药用价值,要想获得或许还得找医铺和药贩子,路锦柏思索片刻还是决定先找洛淮,多番考量选最好的。
关烻这个午觉睡得不错,申时出头忽地就睁开了眼,瞧见路锦柏还在案几前便放下心,坐起身来发现了身上的披风。
他三两下折好放到桌上,上前问路锦柏:“还没看完?”
路锦柏摇摇头,把纸递给关烻,“房屋修缮须得实地考察,今日天色已晚不便前往,我先去找洛大夫了解药材,晚膳不必等我。”
关烻跟上:“我陪你去,也好知晓你究竟病得如何。”
“你来得突然,被盯上怎么办?有阿影阿翔便够了,若是有岔子我回来说与你听。”
“那我扮作侍卫,这总没事儿吧。”
路锦柏没劝过他,由他去了。
好歹是几个大夫共事的医馆,不算狭窄,可路锦柏刚踏入医馆便被发现。
洛淮放下医书迎上来,满脸担忧:“路大人,您是又不爽利了?差个人来唤我便是,何须亲自来。”
“我身子尚可,今日拜访是想向洛大夫请教些学问。”路锦柏言语温和,跟着洛淮往里间走。
洛淮很是受宠若惊“谢大人博学多才不嫌小人愚钝才是。”
关烻最后进去顺手把帘子放下来,“术业有专攻,医药还是得专人来。”
洛淮看了看,问道:“这位是?”路锦柏近身的人他只见过阿翔和阿影,头一回见关烻,还毫无顾忌的坐在路锦柏身旁,不免感到好奇。
“我是路大人的近身侍卫,昨日才来。”
“休要胡闹。”路锦柏瞪他一眼,这才介绍:“这位是定国公幼孙,征西归来的关小将军。不过近来情形异常,他不好暴露身份,人前你别显露。”
他这眼神对关烻毫无威慑力,反倒让关烻觉得有趣,对着准备行礼的洛淮笑:“不必多礼,你也快坐下,今日有得忙呢。”
正事要紧,路锦柏取出纸张,挨个询问。
“若是你们医馆能拿出这么多种子,我也省了不少麻烦。”
“紫苏子不是难事,鹿衔草不易得,医馆也没有多少能分株栽植的,您若是下定决心要救南阳于水火,我便去其他医馆讨来,任大人吩咐。”
路锦柏莞尔:“鹿衔草生长特殊,只怕是不好多种,先紧着医馆用,有多的再送来,可不能本末倒置误人性命。”
“大人说得在理。鹿衔草培养繁复,我得去查医书才能给您写单字,恐怕要耗费些时日。”
“不必,我已从书上知晓,传授给百姓不成问题。”
“大人真是尽职尽责,洛淮佩服。”
路锦柏谦虚言谢,两人你来我往竟互相吹捧起来。
关烻赶忙出手制止,让洛淮给路锦柏把脉,也好让自己有个底。
结果与昨日无异,洛淮把同样的话也给关烻说了一遍。
“我记下了,今日多有叨扰,往后你遇上麻烦尽管来找我。”关烻放下粒碎银,与他那豪迈的语气可不相符。
洛淮发觉他也是个亲民的,不再推拒,一并认下:“仰仗大人。”
还没出医馆,关烻便将臂弯挂着的披风散开给路锦柏系上,好不体贴。
洛淮送二人出来看见这幕,笑道:“您真是心细如发,往后必定也是个体贴的丈夫。”
路锦柏微怔,把下巴藏进披风里。两日温馨,他竟忘了,关烻也到婚配的年纪了。
他是相府嫡长孙,上头只有个年迈的祖父,身后还有个弟弟,路家开枝散叶自是落在他身上。关烻虽是家中幼子,上头有兄姊,可只有他是随父从武的,肩上的担子也不比他轻。
关烻没察觉路锦柏的异样,兀自把人裹严实拉着走了。
水患后南阳的街市便不在繁华,傍晚的路上只有落日拉长了脚步,将整座城照得金光灿灿,耳边回荡着母亲叫孩子归家的呼唤。
路锦柏想起了自己的父母。
母亲生在王室,是受尽宠爱的公主,嫁给父亲时天真未退,满心欢喜要助父亲平步青云。
可父亲志不在庙堂,入仕不过是如祖父所愿,阴差阳错成了驸马,便放下心来专注一隅,与母亲也算是恩爱。
奈何天不随人愿,父亲遭人污蔑通敌叛国,路家一夜之间陷入黑暗。父亲于大牢中被害,母亲郁郁而终,祖父呈上证据才还得清白,可路家已经彻底变样。
路锦柏幼年被封长公子还当是好事儿,在众王子面前展露锋芒,很快便有了教训。懂事后追随父亲,想远离庙堂,同样迫于祖父入了庙堂。
“你要保路家平安,便要恪守本分辅佐君王,大启的史书上,路家只能千秋万代不可遭人唾弃。”
他在官场走得艰难,却不得不走,有时也怨上天,为何让他背负这许多,可还是得接受。
他有时也在夜里想,如果父亲以母亲的助力顺势而上,他今日境况是否会有所不同,可祖父又说,王上忌惮路家,稍有不慎便会株连九族,他想不明白,王上为何对一个落寞世家再三防范。
吃过晚饭,路锦柏说身子不适要早些睡下。
“等会儿,你喝了姜汤再睡。”关烻叫住他。
忙了整天路锦柏已是累极,又不好拒绝关烻的好意,只能撑着意识给祖父写信:
恭请福安。久未来信实为不孝,待回京任凭祖父责罚。孙儿治水工程尚且顺遂,查案还未有眉目,归期未知,孙儿自会保重,祖父不必忧心。
结尾有几句交待与关烻的相处,又觉不妥,舔笔抹去。
心中烦闷,他也不顾笔墨未干,草草收起便交给阿影。
好在没一会儿关烻便来了,他边走边说:“徐季是个粗心的,我得亲自来看着你喝,不叫你犯懒躲过去。”
路锦柏好笑道:“我何时如你所说这般?”
关烻不反驳,把热姜汤端过来吹了吹才交给路锦柏。
“你喝药总要吃蜜饯,奈何南阳没有,你且忍忍吧,回京我再给你补上。”
路锦柏自己搅弄着汤匙,“我又不是孩子吵着要颗蜜饯,何况只是姜汤,温热了也不难下咽。”
没想到关烻忽然变戏法似的拿出块儿饴来,“你把这碗姜汤喝了,我就给你。”
分明是逗孩子的话,对路锦柏却也很适用,他又对着碗沿吹吹,汤匙都没用一口喝下。
关烻递上方帕给他擦嘴,笑道:“你急什么,我又不爱吃,都给你留着呢。你每日乖乖用药,我就给你。”
路锦柏擦完嘴把手帕放下,从衣袖里掏出自己的手帕来:“你且用我这个吧,明日洗净了再还你。”
“我回去洗洗便是,不妨碍,不过你可又欠我一次。”
路锦柏没想起来,语气犹疑:“欠你手帕?”
“当然不是,”关烻正色,似乎怕路锦柏真忘了:“去灵泉观时我娘给我的香囊丢了,你说要补我个开过光的,修竹是要反悔了?”
路锦柏想来言出必行,自然没忘,他早早准备好了,不过是没来得及送出,搁置久了确实有些忘了。
“我记得,香囊就在家中,回京我便给你。”这下轮到他来哄孩子了。
听到满意的回答关烻不闹了,收好东西好让路锦柏休息。
关烻把东西交给徐季,独自去了接头人暂住的屋舍。
清晨收到宫里那位大人的信,查案还得从接头人入手。没有证据抓了外邦人反倒会引起两国纷争,他们这行人担不起这样的罪名。
目前已经确定,接头人并不是南阳人,只是每月来短住几天,说是“探亲”,有时还是不同的人。
位置在城西不起眼的街角,有树木和商贩遮挡,白日热闹时也并不瞩目。
关烻照着徐季画的图纸在周围绕了两圈,确定没人瞧见不会被当成贼才用轻功上了院墙。
没想到这还是个一进一出的院子,关烻不禁猜测这上级恐怕是个财大气粗的庸人,竟如此掉以轻心,连守卫都没有。
又忍不住想,难不成之前遇害的几位大人也是轻易察觉异常来调查,才被灭口的?
可他们现在的动静也不算小了,路锦柏虽有所隐藏但到底不算周密,总有走漏风声时,这些人不可能没知觉。
躲在驿馆自然不会有人来送死,那为何今日在路上也没有人来动手?
他们下手究竟是为何?
关烻满脑子疑惑,拿出徐季给他准备的迷香。
为了查案,做一回小人又如何。
他摸到接头人住的屋子将迷香都扔进去,半点不留,等迷香散淡了才进去。
关烻草率了,推门便是接连几发暗箭,若不是他身手好真得受伤,甚至中某种奇毒当场身亡……
心有余悸地看了看床上躺着的人,确定他没有醒来的迹象,这才又往里探,不过比先前谨慎许多。
几乎把屋子翻了个遍也没找到有用的东西,关烻把目光转到接头人身上。难不成,在他身上?
蹑手蹑脚在床便摸索一阵,关烻翻到张写满外邦语言的字条。
阿翔说几人同酒楼小二交谈都是用大启官话,屋内谈话则用外邦语言,眼下连重要字据都用外语,想来那接头人的上级也不简单。
贸然拿走势必会打草惊蛇,关烻拿出块儿黑炭,依葫芦画瓢临摹下来,好供他侦破。
不过他又有些怀疑,这会不会是假的,就等他上门来中计?
犹豫片刻还是想先带走,听听修竹怎么说。
出来得不巧,正好遇上打更人,见他从院墙跳下来把他当成了贼,作势要大喊抓贼。
关烻庆幸自己穿了夜行服还戴了面罩,旁人看不出来,眼疾手快在他出声前给敲晕制止,拖到墙边安置好才离开。
路锦柏昨夜喝了姜汤泡过脚,睡得极好,一大早精神极佳,见了谁都满脸笑意,用过早饭不等关烻来便动身前往郊外考察破损的房屋。
洪水过后的大地上满目疮痍,贫瘠的土地散落着村民的用具,有人在修缮房屋,有人在捡破烂。鼻尖嗅不到林间芬芳,反而是恼人的腐臭。
路锦柏心头酸涩地看了许久,抬脚走近记录。
结合灾民的自述,只有几间被大水冲得无影无踪的茅草屋需要重建,其余只需修葺。他虽不擅长,但村民是会建房子的,他备好木材和茅草便是。这些人都是相熟的邻里,搭把手不是难事,加上他派的人,很快便能重建村庄。
洪水退去的田地已经看不见之前栽种的菜,只留下踩一脚便黏着鞋掉不下来的土壤。
不过很快便能恢复原样了。
路锦柏在脑中规划村民食用的蔬菜和药材栽种的位置,大概记下便着人安排。
不出半日,木材和茅草都已备好,蓬头垢面的灾民们不约而同朝路锦柏跪下,“多谢大人,大人您就是咱们的再生父母啊!”
路锦柏受不起,慌忙让众人起身,哭笑不得地安抚一哭就停不下来的孩童。
“路大人。”路锦柏回头发现关烻提着食盒来了,又是昨日的侍卫打扮..
“怎么不等我?我要来寻你还被陈大人给抓住,让我去收齐了药材种子才放我走,还千叮万嘱不要让人注意。”关烻走近了抱怨。
路锦柏接过食盒打开,把糕饼都分给孩子们。
关烻也蹲着帮忙,等人都散了才掏出他私藏的有人脸大的蟹黄饼,“给你的,我不私留一块儿你便打算饿死自己?”
“饿这一顿不成事,这些孩子难得吃上,给他们吃些又如何。”路锦柏对着蟹黄饼眉眼弯弯,“你是有意带糕饼好让我分给他们?”
关烻坦率:“路大人刚来南阳给孩子分饼我可是在边塞就知晓的,不敢跟您抢风头。”
路锦柏不理他,专心吃起午饭。
“你怎么不问问我吃了什么?”关烻突然问。
路锦柏闻言嘴里的饼都忘了嚼,含糊着问:“你没用午膳?”一边把手里的饼递给关烻,“我尚且不饿,晚点儿吃也无妨。”
“修竹总说我像孩子,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关烻没接,悠哉悠哉走到堆成山的木桩边翻身坐上去,“我就想知道,把百姓看得更重的路大人会不会也替我这小小侍卫考虑,看来还没到那个份儿啊。”分明又是在胡闹。
路锦柏无言以对,表情淡淡地站在原处细细咀嚼口中美味的饼,两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气氛古怪。
不知情的阿翔赶过来,“公子,陈大人催您回去有要事商议。”分明是耳目清明之人,此刻却完全忽视了不远处的关烻。
“我随后便来。”路锦柏加快速度,动作仍不显粗鲁,看得关烻忽然也想尝尝他那饼的滋味儿了。
不过他没动。
得等着路大人来求他护驾呢。
路锦柏仔细擦了嘴,歪头看了关烻一眼,径自走了。
被打个措手不及的关烻跳下来跟上,给自己讨说法:“路大人好大的官威,被戳破不体恤侍卫还无动于衷,真不怕侍卫恩将仇报。”
“你要如何恩将仇报?”路锦柏头也不回地配合他胡诌。
关烻背着手,得意得很:“要让路大人每日陪我用膳,我没放筷路大人也不许放筷。”
路锦柏眉头微扬,瞥眉道:“你这侍卫书都白念了,恩将仇报是这么用的吗?”
“那该如何?路大人玉树临风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教教小人吧。”
路锦柏睨他一眼,关烻急忙住嘴,又是个听从命令的侍卫。
厅堂里没人坐着,都围在桌边讨论着什么。
路锦柏也加入其中,看着炭笔写得歪歪扭扭的外邦文字和译语官誊写的大启文字。
灵药奇效,半指伤本,一指毙命。
短短十二个字却让在场所有人愁眉不展。
一来不知这药在哪儿,二来不知要用到谁身上。
倘若是对在场诸位,直接下手便是,何须再往上报?
最后看到译文的关烻立马就明白了,惊叹那药竟然这么厉害,如若没能偷换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萧艾珏问徐季:“这是何人送来的消息,是真是假?”
徐季答:“昨夜我家将军外出时遇上蒙面人,蒙面人不及我家将军,化了迷雾逃走,只留下这信。”
路锦柏惊讶道:“你怎么不同我说?”
“咱们都不懂外邦文,我想着等译文出来再告诉你也不迟。”关烻心虚地挠头。
“蒙面人为何要帮我们?”
关烻灵机一动:“兴许是江湖侠客处江湖之远仍忧其君,特地来助我们查明真相。”
他年纪轻不稳重,又是个不爱读治国策论的,说出这样荒谬的话也没人说他,全当没听见,兀自讨论。
陈勖最终还是写信派人八百里加急送往京城王上手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稍有疏漏便是大罪。
众人散去各司其职,路锦柏将关烻带进房中,“究竟是何人给你来信?”
相处多年,关烻主仆二人的话可瞒不过他。
什么样的蒙面人能在关烻眼皮底下放迷雾逃跑?又为何不惩治张正恩?
关烻的视线不断掠过房内各处,就是不敢对上路锦柏的眼睛。
关家与那位大人的事说来话长,他今日把真相告诉路锦柏,明日那大人便能知晓,关家人的安危也不是定数。
思来想去他只能保留,神色恹恹:“是我去偷来的。”
路锦柏不可置信:“你昨夜去的?为何不告知我,若是有埋伏你今日还能站在这儿吗?”
言辞分明是关心,关烻却抓错了关键:“修竹你担心我?不觉得我有辱斯文?”
路锦柏恨不得给他一拳,“你在边塞究竟怎么打的胜仗?”
说起这个关烻可不迷茫了,但还是知道路锦柏在生气,连忙哄他:“我都是探明没危险才去的,也算是立了功,修竹不与我这等小人置气,身子要紧。”
倒是让他躲过了质问,二人又恢复从前那般。
陈勖带蒋英在村庄监工,萧艾珏和路锦柏查案,关烻时常提出鲜少被注意的问题,意外挖出更多线索。
几日后,外邦人正常离去,几人分散查入当铺,将管事人都抓起来。
关烻带人进入离驿馆最近的当铺时,账房管事鼠一样细小的眼睛顿时瞪大,笑得虚伪:“不知如何惊动了官老爷啊。”
关烻扫视完整间屋子,面色不改挥手命令:“把人扣下,铺子封起来,别叫人说我们偷他东西。”
管事骤然发怒:“我什么都没做,你凭什么抓我?你是什么官,张大人知道了你可没好果子吃!”
“你跟张大人很熟啊?那你便去大牢见他吧。”关烻冷着脸笑,犹如地府爬上人间的恶鬼。
张正恩的底细他们早就查清,说这话只是想让他知道自己如今的处境,安静坐在地上待审总比被绑起来堵住嘴舒服。
没过晌午,众人随萧艾珏出现在大牢刑房,当然,蒋英并不在列。
几个管事被绑在木枷上,一改刚才的嚣张气焰,直喊冤枉误会。
“怎么是误会,你东家什么人你会不知?”萧艾珏坐上太师椅,路锦柏自觉当起刀笔吏。
“我东家是是名正言顺来南阳开当铺的,能通行于两国的使者。”
萧艾珏讽刺道:“不面见君王而私自勾结下吏换取消息谋害大启官员,这是帝国间谍,你们帮他收集情报,同样是要杀头的。”
常人听到杀头之罪必然惊慌,这几人却极力辩驳,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外邦人。
路锦柏与萧艾珏对视,摇摇头,放下笔走出刑房。
很快,惨叫声直通地底,从四面八方将路锦柏包裹,听得他头皮发麻。
直到有人求饶,关烻来叫他回去。
“我这当铺本是自家的,十几年前被位大人罢了去,说只要帮他收集消息,给外邦人个名头,他便把当铺交还,否则我全家性命不保。我也知道这是重罪,谁又愿意背弃母国呢?我试过传递假消息,可都被识破了,我和老父老母险被打得丢命,我与娘子的孩子胎死腹中啊……”鼠眼男说着哭了起来。
男儿有泪不轻谈,只是未到伤心处。
关烻双手抱胸倚在路锦柏的椅子旁,发现路锦柏的字迹都受了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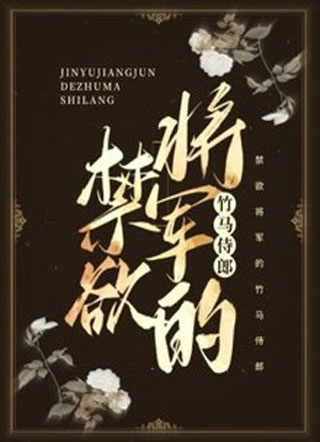
作者:林怿昔类型: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