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王的独宠》的主角是花知节沈拂霜,是作者六崽所著的一本纯爱小说,小说蛇王的独宠主要讲述了:沈拂霜他不想要在继续想当年的事情,他觉得这样难受的人只会是他自己。网友热议:既然过去了就让他过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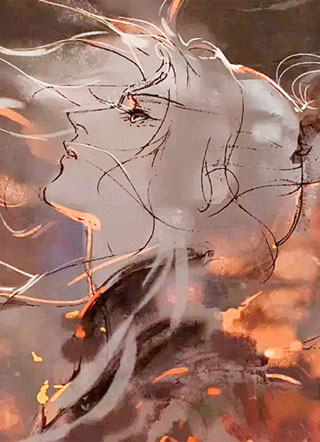
来源:废文 分类:现代 作者:六崽 主角:沈拂霜 花知节
下午,花知节坐在城里最热闹的茶楼里听说书,讲的是赵子龙救阿斗的故事,他点了壶今年新上的雨前茶,并甜咸两样点心。台上说书人不时地拍响惊堂木,把一节糜夫人托孤投井说的声情并茂,叫人唏嘘不已。
花知节混坐在人堆,漫不经心地睃视左右。茶楼热闹归热闹,但没有满座,中间最好的位置只坐了两桌,旁边次等的位置同样未满,三等和末等的茶客最多,每桌仍旧还是有一两个空位。
“小郎君有什么吩咐?”
他看稀奇多看会儿,角落里候场的小伙计立刻小跑过来低声询问。
花知节的眼睛飘向隔壁桌子,无话找话地问道:“他们桌上摆的那是什么?”
小伙计扭头看了眼,答说:“椒盐片,本地的特产,小郎君也来一碟尝尝?”
花知节点头默许,伙计很快拿来一碟椒盐片,跟着的还有位年轻人:“小郎君,这位郎君相与您搭个座,您看方便么?”
花知节先是瞧见熟悉的衣摆,再抬头往上看,果真是借了他衣衫穿的顾蔚冉。她冲着花知节眨眼,拱手道:“贤弟,久未见面,可还认得愚兄?”
也不知怎么回事,片刻未见,顾蔚冉的嗓子略有几分低沉,嗓音沙哑,确实有些像男人。
花知节陡然一惊,他没想到顾蔚冉说的“自会一见”竟然是在这里见。两人在客房分别,顾蔚冉沿着原路从窗台翻出去,临走之前她与花知节说好——你且管你玩,稍后我俩自会一见。
“……”花知节也跟着她演戏,微微地颔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忍笑道:“兄台自便,恕在下眼拙,不知兄台高名大姓。”
顾蔚冉从容入座,说:“不过几年未见,贤弟竟忘了愚兄,弋阳谷的顾朝,贤弟可有印象?”
她说了个半真不假的名字,世间果真有弋阳谷,也的确叫顾朝的弟子,不过这人昔日门内比试落败,罚自己闭关经年,已久不入江湖。
花知节连忙作出恍然大悟的模样,说了几句客套话,令伙计依葫芦画瓢地再上一份茶水点心。
“原来是顾师兄,见谅,见谅。”他屈着两根手指在桌上轻叩两下,“少时一别,经久未见,倒是认不出师兄了。”
顾蔚冉从容入座,瞧了瞧台面,双眉紧皱,嫌恶道:“点心撤了,茶换成明前,我不喝雨前。”
伙计哎一声,端着茶和点心走开,顾蔚冉往花知节旁边靠过去。她摸着下巴,低低地说:“你右手后边,那个叫卖栀子的小丫头,我见过她好几次。”
花知节只是眼神往后轻瞟,并没有顺着话音回头去看。他依稀有见一抹白影在人群里穿梭,又偏过头凝神细听——人堆里混着一道细小却十分稳健的呼吸声,以他的经验,这人有些功夫底子,但也说不上太好。他正听得仔细,忽然台上惊堂木骤响,原是这一折说完了,要换别的人来讲下一折。
人群松动,三三两两地有人起身离开,也有坐着等听下一场,比如花知节与顾蔚冉。她换了明前茶,另外单要了碟花生,坐着慢慢地剥。花知节始终追听那细微的呼吸,中间穿插了小女孩甜脆的叫卖声。“栀子花,新鲜的栀子花,戴一朵香喷喷。”
声音越来越近,几乎就到了花知节的耳边:“小郎君,买一朵栀子花呀。”
花知节转头,恰好对上买花小丫头的视线,她笑眯眯地拿着朵花递到花知节鼻尖前,馥郁甜香顿时如无形的网兜头兜脑地向他笼来。花知节只觉自己紧跟着就是神思一晃,心神骤散,隐约有不对劲的感觉。
他木木地坐着发怔,冷不丁有只手在他身上一抚一拍,接着就横插进来来夺走小女孩手里举着的白栀子花。
“这花长得真不错,我来两朵,正好拿回去,摆在佛前清供。”她捏着花枝,把花搁鼻子底下闻了闻,满意地点头,“小娘子,这篮花几多钱,小爷都要了。”
卖花姑娘听了这话,霎时喜不自胜,抱着篮子,娇声说道:“郎君府上哪里,奴与你送去呀。”
顾蔚冉把花枝抛回提篮,捏过花枝的手指依旧有甜香萦绕:“小爷府上在外地,奴奴恐难送去。我们兄弟初来乍到江州城,还没想好住哪里,小娘子可有好地方介绍?”
她笑嘻嘻地说话,眼神轻佻地从卖花姑娘面上滑来滑去,把人盯得红了脸,娇娇地垂下头:“奴晓得一家新客栈,除了地方有些远,别的都是顶好,郎君可愿随奴去,好叫奴赚点跑腿钱。”
她们你来我往讲话的功夫,花知节愈发头脑昏沉,神思涣散,如坠迷雾。顾蔚蓝的一拂一拍,令他稍微几分清明,随着花香丝丝缕缕钻进鼻孔,渐渐地又陷入混沌。
他迷糊中听见卖花姑娘出言想邀,也没听明白究竟是去哪里,就楞楞地站起来,嘴里翻来覆去地呢喃道:“好……去……去……好……”
他从座位上站起身,两眼直勾勾地盯住卖花女,她身形往哪动,花知节就跟着她往哪边摇摆。
这会儿新的书已经开始说起来,茶馆里人又少许多,于是他们这桌显眼。卖花姑娘似是不愿被人瞧着,忙忙地向外边跑:“那说好了呀,郎君。奴就在门口候分外着,郎君们记得一会来找奴哦。”
她捧着花篮子急急地往外跑,只见花知节身形微动,竟仿佛是要跟着同去的 意思。顾蔚冉伸手捉住他的衣袖,用力扯住,另只手伸入茶杯里沾湿了往他脸上轻弹。
花知节陡现出几分清明,疑惑地盯着顾蔚冉。
“你中迷药了。”顾蔚冉低声嗤笑,“她的篮子里有两种花,一种是普通栀子,一种是掺了迷药的毒栀子。她给你闻的就是藏在底下的那种。”
花知节难以相信:“你也闻了,你怎么没事?”
顾蔚冉越发笑地欢畅:“贤弟不知,愚兄号称毒祖宗,凭她这点末流手段,压根不入我的眼。”
接着,她从腰带里翻出一个纸包,打开挑了点药粉撒进花知节的茶里,关照他立刻喝下:“趁手东西都不在,多少有些为难。这是我临时配的,你喝下去可保神志清明。”
花知节盯着面前的茶汤,心下略有几分不信。他暗恨自己今回冒失,原本想看个热闹,现再却像是把自己变成了热闹。他没动那杯茶,整个人木木地坐着,四周里还有点花香余韵,渐渐地他的神志又陷入昏沉。
他什么都想不动,也听不清,也看不清,顾蔚冉的身影变得遥远,戏台更是天边一道红红的虚影。
花知节又想起身,他吸吸鼻子,只觉微微地甜香很是勾人。
顾蔚冉见他又是一脸空茫,知道是残留的药劲上来了。这回她不待花知节想明白,径直一手捏住茶杯,一手捏住他的嘴,把一盏半冷茶水硬生生地灌进去。花知节木楞楞的,倒是没有挣扎,就是老要站起来,顾蔚冉只得用手按住他的肩,逼着他静坐等药起效。
约莫过了一刻钟,顾蔚冉吃完两碟花生,花知节才缓缓地回神。顾蔚冉没事人地坐着听戏,见他双目逐渐有神,笑眯眯地推了一碟剥好的花生米到他跟前,戏谑道:“小兄弟,令师长竟放心你孤身下山?”
花知节讪笑,赶忙拿起茶杯,却发觉杯子已经空了,不知觉间,花香的味道也淡得几乎闻不见。
“你若还行,我们不妨先出去,路上再细说,”顾蔚冉拈一粒花生米投嘴里,“门口的小娘皮心急如焚,一直往这瞧,生怕到嘴的鸭子飞了。”
她起身走到花知节左边,右手垫在他的手肘,竟是轻巧地把人托了起来,步履稳健地往门口走去。买花姑娘挽着篮子等在门口,她的生意似是不灵,篮子里的栀子花竟是半点未见少。
顾蔚冉探头瞧这她的花篮,装模作样地责问道:“小娘子,已经是我订的花,可曾趁我不注意卖了两朵与旁人?”
“郎君惯会说笑,既是你已经定下的花,奴又怎会予旁人。两位郎君,奴这就带你们去瞧客栈可好?”
她着急带路,连走两步忽觉身后两人没跟上,不由得停下回望。
顾蔚冉暗中捏了下话花知节的手肘,后者马上心神一散,站不稳似的整个人往旁边倒去。顾蔚冉赶忙接着他,两个人身高差有一拳,顾蔚冉身形单薄,撑着比自己高壮的花知节看着很吃力。
“先不急,小娘子可知哪里有医馆,”顾蔚冉勉强摆手,“我这小兄弟不知怎的,忽然神思恍惚,状若痴呆,我想先带他去瞧个大夫。”
听到他的话,买花姑娘脸上飞快地闪过一丝诡谲的笑意:“郎君,勿忧,客栈旁边就有医馆,郎君跟着奴走就是了。”
看她的意思,今天不管怎样,这两人都非得跟着她走才行。
她也走来扶着花知节,浓甜的花香又近身前,花知节悚然大惊,恨不得立时逃开这里,可惜左右胳膊都被人搀紧,便是想抽修身而逃也不行。
卖花娘领着他俩走街串巷,过了七八处桥,顾蔚冉拖着花知节,走得额角汗都冒出来,传说中的客栈还没有走到。花知节被人托住手肘,拽紧了就是一通猛走,他装傻不敢擅动,整个人被甩来甩去,心气浮动,几乎当场呕出来。
正在他快要放弃好奇心的时候,卖花娘指着对面一处簇新装饰的客栈,欢喜道:“两位郎君,就是这里,奴送你们进去,顺便好向掌柜讨几个赏钱。”
花知节觑眼偷看,竟真是间客栈,还是间新开不多久的客栈,店里看起来有些暗,稀拉拉的似乎没有几个人。他又偷看顾蔚冉,她面色沉重地盯着眼前的客栈,视线来回睃视,似是要扒墙缝把里边的转头都拿来熟仔细。
“等会儿进去里面,一应吃喝都不要碰,闻到香薰马上闭息。”她与花知节附耳关照。
花知节犹在装傻,霎时之间,只是微微点点下巴,算是自己知道的意思。
卖花娘进去不多会又出来,喜滋滋地说:“多谢两位郎君,奴的赏钱赚到了。郎君,你要的栀子,奴已悉数都托给店家,掌柜说,等等摆进郎君看中的房间里。”
说话间,客栈掌柜带了小二迎出来,一人接过昏沉的花知节望店里去,一人笑眯眯地躬身请顾蔚冉进店瞧瞧。
“小店虽是新开不久,但一应都是好东西,郎君进来瞧了便知小老儿句句属实,半点瞎话也没有。”
掌柜陪着顾蔚冉同走,这客栈看起来门面不大,内里却是干净整洁,处处透出几分精巧。顾蔚冉左右睃视一番,啧道:“瞧着还行,来两间上房,再去请个大夫过来,我这位小师弟忽然不舒服,记得请个好大夫过来瞧病。”
她往柜上抛了块拇指大的碎银子,又说:“小爷路上行李丢了,找人买几套好衣裳来。钱从账里一并出,不够再找小爷添。”
难见她这样豪爽的客人,掌柜真是笑得眉眼不见,急忙招呼小二送两人到楼上客房。两人的房间在三楼,是相邻的两天天字号客房。顾蔚冉指挥小二把花知节架到床上歪着,随机冷着脸,令他们速去请大夫过来。
——我这小师弟金贵着呢,若有半点闪失,怕是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她原话就是这么说,小二忙不迭地应声而退。亟待两人走出房间,花知节马上翻身坐直,冲着顾蔚冉拱手,道:“方才得罪了。”
尽管顾蔚冉一身男人装扮,但他可没忘记她内里芯子可是位姑娘。刚刚为了演戏逼真,不得不紧靠着她,花知节心里多少有些别扭。
顾蔚冉道好似不在意,她在房间里上蹿下跳地仔细查勘,每样东西都拿来摸摸,每面墙都贴上去听着声仔细拍。然而任她如何细搜,都没有查出半点不妥之处。她正纳闷,小二隔着门说大夫请来了,顺便她买的栀子也送来了。
花知节闻声不由苦笑,深呼吸后,又倒回床上。
顾蔚冉应了一声,让任自行推门进来,小二送来茶水点心,手里还提着一捧浓香的栀子,身后跟了小老头,背着个药箱,大约是请来的大夫。她让小二领着大夫去给花知节瞧病,自己伫立在花束前面翻来覆去地看,虽然花还是栀子花没错,数量也没少,但要紧的几支都不见了,现在这就是一束普通的白栀子。
那边大夫瞧了半天没看出什么病症,最后只得猜是天热受了暑气,开了副清火凉血的方子。小二把药方拿给顾蔚冉瞧,她眉头一挑,不耐烦道:“照着抓药便是,给我瞧什么,我又不懂这些。”
说着她随手摸出两星碎银,一星给大夫,一星给小二,让他跟着去抓药煎药。两人刚出去,花知节折腾着想坐起来,冷不丁又被顾蔚冉按了回去,接着走廊上传来一阵脚步声,是买衣服的小二来送衣衫。
花知节见状索性也不起来,侧过身闭目歇起了午觉。
小二煎好药送进来,顾蔚冉接过闻闻味道,随手倒进角几上摆的盆景里。照她的意思,少吃少喝少碰最好,然而她自己却是捧着小二拿来的干果吃个没完。
“你才入江湖不懂,那些下三滥的阴私手段多了去,只要你稍微不留神,就着了他们道了。”她吃完花生吃核桃,店里没有明前茶,她退而求其次地要了壶茉莉香片。
一时间屋子里各色香味弥漫,明冽的栀子,细幽的茉莉,苦寒的汤药,彼此缠绕、纠结、厮杀,仿佛要决出高下才肯罢手。
花知节在床上躺了会儿,被这混杂的气味熏得一个劲直打喷嚏。他实在受不住地从床上坐起,走到顾蔚冉跟前,伸手去抓核桃,却被顾蔚冉拍开了。
她剥开一粒核桃,把桃仁抛进嘴里,笑嘻嘻地劝道:“东西不干净,你可不能吃。”
花知节不信,偏要去抢:“你少骗我,要真不干净,你吃了怎么没事?”
“我天赋异禀,常人羡慕不来的。”顾蔚冉吃干净最后一粒核桃,把满筐的核桃壳倒在台面上,接着从衣袖里头摸出块香饼点燃了搁在核桃壳最上头。
花知节看了眉眼直抽,这房间的气味已经够繁杂了,她竟然还点熏香。然而气味出来之后,花知节再看向顾蔚冉的眼神不由得透出几分敬佩,是很冷的山松霜雪的味道,细烟袅袅间压住所有那些浓糜的气味,还这屋子一片清宁。
像是预料到花知节的反应,顾蔚冉略显得意地摆摆手,堵住了他想说的客套话。
她坐在窗台上盘算眼下的情况,不说不动的时候,她看着有有些拒人千里的冷肃。在她面前,花知节就是端不起架子,明明在门里时,对着那些年长许多的师兄师姐,他都是一贯的冷面寡言,偶尔甚至有些未来门主的骄矜。
尽管,他并无意接任。
顾蔚冉默默地想了会心事,回神后瞥见呆立身旁的花知节,竟是吓了一跳,纳闷道:“你站这里做什么?”
花知节偏过头好奇地打量对方,提出了自己的困扰:“顾姑娘,你看着跟我差不多大,为何对江湖事这般老练?”
顾蔚冉闻言直笑,说道:“我十岁上就在江湖浪荡,至今已是七年有余,你说我熟不熟。”
她从窗台一跃而下,拣出燃尽的香块扔出窗,拍拍手说:“走,咱们先去吃顿好的,我再去找几样趁手家伙,今晚恐有一场恶斗。”
她做足戏,像个好大哥似的揽着花知节的肩膀一同出门,然而她比花知节要矮上些,这般勾肩搭背,闹得花知节百般不自在。他挣了几下,却是挣不脱,顾蔚冉搭在他肩头的胳膊特别稳,压得他像只鹌鹑般缩头缩颈。
两人打账台前走过,掌柜特地绕出来瞧了花知节的情形,看他这会儿神清目明,连忙念了几声阿弥陀佛。他问两人去哪里,又说花知节的药还有一付,晚上可要煎好预备着。顾蔚冉含糊地支应过去,说两人出门玩玩,见识见识江州夜景,晚点再回来。
“掌柜,那药晚些煎好了放我小师弟屋内就行,”顾蔚冉吩咐道,“晚些我们回来,我自会盯着他服用。”
他们走出老远,花知节才小声地问:“顾……顾师姐,这间客栈可有问题?”
顾蔚冉的手还搭在花知节的肩头,听了这话,不由失笑:“我算你哪门子的师姐,熟人都管我叫‘小顾’,你也跟着这般称呼即可。这间客栈看起来倒没有什么问题,但这里的人、就未必。”
“可我年头刚十六。”花知节此刻已是对她有了几分钦佩,因而不愿怠慢,“哪能叫你‘小顾’,这不合适。”
顾蔚冉又是摆手,说:“那有什么打紧,不过差个一岁,你我不说,有谁知道。我要去准备些东西,你要跟着一起来么?”
花知节想着左右自己无事,与其四处乱晃,不如跟着顾蔚冉,说不定还能再长点见识。他和武令君性子静,两人都极少下山,便是难得的几回,也不过到镇上逛逛大集,买些山上没有的饮食而已。
要论江湖的规矩,花知节当真是如张白纸。武令君还来不及同他细讲,就先走了,他贸然下山,多少有点羊入虎口的意思。
当即,他决定无论如何,今天都要跟着顾蔚冉。
他们在街上东转西转,不知不觉竟走回了最初的那间茶楼,顾蔚冉领着他从门口走过,再转了两次,转进一间准备打烊的绸缎铺子。伙计刚想轰他俩出去,在看清顾蔚冉的面孔以后,神色一凛,放他们进去店里。
顾蔚冉走进店里,四下瞧了瞧,说道:“我的包袱被人偷了,趁手家伙都没了,找你们掌柜要几样小玩意。今天晚上,你们警醒些,我已经摸到那些人的老巢,准备陈趁夜宿去探探,你们也留神,少不得会有一战。”
伙计找来掌柜,掌柜已知客是顾蔚冉,甫一进屋就躬身拜道:“不知小谷主来,有失远迎。”
顾蔚冉点点头,应道:“无妨,我也是临时起意从江州过。刚跟你伙计说呢,我的趁手家伙都没了,你这儿存着些什么好玩意,都拿来让我挑挑。”
她说着,从衣袖里掏出块毛边绣片,扔给掌柜细看。花知节规矩地站在边上旁观,他看这片布头甚是眼熟,偏头想了会,恍觉竟是从顾蔚冉衣服上撕下来的。他张张嘴,不知道说什么合适,显然他借出去的这套衣衫是凶多吉少,难以要回了,
掌柜接过毛边绣片,借着西沉暮光仔细分辨上头绣着的图样,花知节赶忙也跟着瞧,他看了许久,才依稀看出那是个三条尾羽的鸟。
他还是头回见到如此稀奇的怪鸟。
掌柜验看过毛边绣片后,立刻引着顾蔚冉往里间走,花知节见状也准备跟去,却被掌柜侧身拦下:“少侠,请留步,且在此处稍等,小谷主片刻即来。”
花知节只好停在原地,等不多会就见掌柜把人送出来。顾蔚冉和进去前一样,甩着两袖清风走来。他也看不出她到底预备了什么,明明手上连柄剑都没有。花知节正预备问,转念想到既是顾蔚冉的趁手兵刃,想来亦是她门派私密,便歇了念头。
及至走出绸缎铺子,花知节方后知后觉地问了句:“刚才那个掌柜称呼你‘小谷主’,你家是……?”
顾蔚冉惊诧地瞪他,说:“原来你不知道啊,我爹是弋阳谷顾锦衣。”
花知节讷讷地啊了声,武令君从不讲江湖事,他也没想过要问。他压根不晓得“弋阳谷”是什么地方,顾锦衣又是什么人,但看她说来得意,只能胡乱点头应和。
随后,他继续跟在顾蔚冉的身后看她进各种铺子,买了许多零零碎碎的小玩意,然后让店家送到客栈去。花知节看她花钱如流水,隐隐察觉有些不对,忍不住问道:“既然你的包袱丢了,那这银钱是哪来的?”
“也是你的,放心,我记着账,到时一起还你。”顾蔚冉安慰道。
猜想被印证,花知节一时间无言可对,苦笑着继续跟在顾蔚冉身后,这回他们踏进一处青楼。起初他未留意,等回神已经站在楼内,鸨母满脸堆笑,招呼娇娘子来见客。霎时,他面白如纸,身形打晃,赶在娇娘们涌来前,落荒而逃。
迟些,顾蔚冉拿了物件从青楼出来,瞧见躲在路边缩成一团的花知节,不禁有些奇怪。她以为花知节是见不惯这种场面,正待打趣,却见他面容失色,竟是蹲在这里干呕。
这是她始料未及的情形,她还是头回见有人纯情如斯,只因为入青楼片刻就扶墙干呕。她想笑又觉不妥,一路憋着笑一路搀着花知节回客栈。花知节跟在她后头,神态萎靡,许久才渐渐地舒缓过来。
“见笑了,我……我不习惯这种地方。”他低声解释。
顾蔚冉忍笑摆手,说道:“无妨,多去几回就习惯了。”
花知节没有接话。
他们走回客栈,店里亮着灯,有几桌人在堂上吃饭,顾蔚冉一行走一行看,眼睛盯着别人桌上不住地瞧,末了唤来小二,让人依样给她送一桌到房里来。
她不让花知节吃店里的东西,自己却吃起来没完没了。
花知节参不透其中玄妙,权当她真有百毒不侵的天赋。
及至深夜,花知节洗漱妥当,将将躺到床上,忽然窗台那边传来悉索的动静,接着就是有到人影蹑手蹑脚地从那里翻进来。这熟悉的一幕,令他无话可说,拥着薄被坐在床上瞪着顾蔚冉。
顾蔚冉朝他摆手,劝道:“你自睡你的,我到梁上坐着就行。”
说着,她足尖在椅背一点,身形微动,倏地跃上房梁躲了起来。他们的房间在三楼,房内各有一根房梁当屋穿过,顾蔚冉藏在那里正合适。
花知节掀开被子跳出来,他想去房梁上同顾蔚冉论个道理,无论如何,大半夜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总归不太对劲。
谁想顾蔚冉压根不给他这个机会,飞快地从房梁跳下来,一边嘴里嘟囔着,忘了,忘了,差点坏事,一边从怀里摸出个小白瓷瓶,打开在花知节鼻下轻晃。花知节只记得这味道似曾相识,跟着就软身倒下。顾蔚冉又拖又拽地把人重新摆回床上,拉来薄被盖他身上。
随后,她重新躲回房梁上。
此夜漫长,顾蔚冉在房梁静候良久,才等到屋里再起动静。
房门被轻轻地打开,走进来四五个人,为首的赫然是白日里那个见人就笑,说话和气,有求必应的掌柜,他指挥小伙计到床上搬人。四个小伙计,搬手的搬手,抬脚的抬脚,麻利地把呼哧大睡的花知节往外搬。
顾蔚冉缩在房梁静观,见花知节被抬走,忍不住在心中默念一声,得罪了。
小厮们搬着人先走,掌柜在屋里盘旋了会,方慢吞吞地离开。顾蔚冉对着他弹了弹指甲,一点细碎的粉末落在他肩头。
他们搬了人径直往后门走去,那里停着辆单套驴车,掌柜挥退小厮,自己坐到车头,抖着缰绳指挥驴车往城外跑。原本客栈位置就偏,何况河对岸的树林子后,有处残垣,从那里出城,并没人会察觉。
顾蔚冉一路远远吊着,眼看驴车走到城外一处山神庙前停下,掌柜上去叩门,短——长——短,叩了三下。破门吱牙打开,里面走出几个穿金戴银,打扮艳丽的女子,中间就有白日里见过的那买花娘。
只是这会儿,她长发梳髻,簪花戴柳,穿一件轻薄半透的衣裙,露出好大一块胸脯肉,瞧着像个不太规矩的美妇人。她同掌柜让到一旁说话,另几女子笑嘻嘻地拥到车前抬人。
她们掀开车前布帘,瞧着里面沉睡的花知节啧啧赞叹,欣喜地伸手进去又摸又捏。在掌柜来搬人之前,顾蔚冉已经去了花知节面上乔装的旧疤,此刻他看来就是个姿容无双的俊俏少年。
她们抬了人正想进庙,忽然间,顾蔚冉笑眯眯地从天而降,落到破庙的门檐上。
她居高临下,望着底下大惊失色地几人,问道:“掌柜,更深露重,这是要带我的娇娇小师弟去哪里戏耍?”
这会儿,她换回了自己那件素白劲衣,衣摆处缺了一角,毛拉拉地荡出几股经纬线。
掌柜好似一时没认出她来,喝问:“你是哪来的小瘪三?”
“弋阳谷,顾朝,顾蔚冉,”她站在檐上,右手握着一柄做工精巧的小弩,左手扣着三枚细针,针尖淬了毒,盈盈泛着蓝芒,“阴素水,王珣,我劝你俩动手前想清楚。”
夜风吹起她的辫梢,她笑嘻嘻拨开的模样叫人瞧着火大。
庙门口,卖花娘阴素水,掌柜王珣互相对看一眼,各自腹诽对方是个蠢货,竟惹来这个瘟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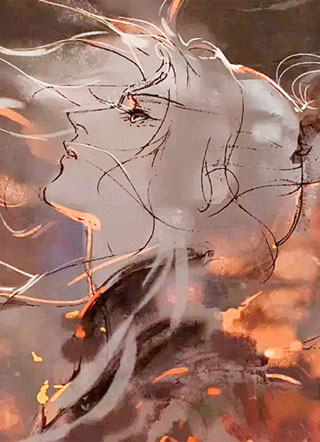
作者:六崽类型:现代
都是爱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