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对头们每天都在逼我把水端平》是由作者沈百万所著,和祝是小说死对头们每天都在逼我把水端平中的主人公,主要讲述了:和祝根本不爱任何人,他把死对头当死对头,可他的死对头都把他当爱人诶!热议:是他的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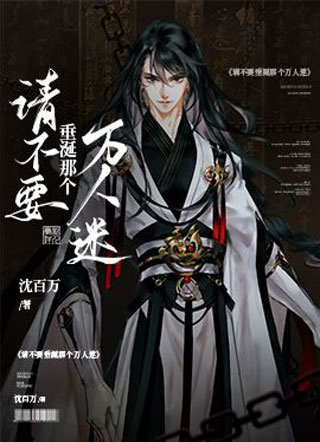
来源:书耽 分类:现代 作者:沈百万 主角:和祝 和祝
低沉的声音里掺着蜜,轻挑又认真。
脚下是饱满柔韧的胸肌,蜜色的肌肤细腻光滑,眼前是牧蕴舟一点点凑过来的俊秀脸颊。
灼热的气息扑在脸上,和祝脑子轰一下炸了。
早知道他是个混不吝,却没想到他敢把主意往自己身上打。
身体比脑子反应更快,和祝抬脚压下他的肩膀,起身掐着他的脖子,将他整个人都按在了榻上。
这是一个极具羞辱意味的姿势,脸朝下头被死死按着,和祝一只脚踩在他的腰部,全身的脆弱点都处于桎梏之下,一种诡异的兴奋感从腰椎骨迅速向全身蹿开,牧蕴舟无声地勾起唇,讨饶的话出口却正经无比:“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得鱼忘筌,看来药劲儿是过了,力气这么大呢?”
“荣王殿下教你习武,你就用来欺凌我这弱小?”
“和祝!我要是闷死了,你也别想活!”
……
他说了一大串,和祝耳朵只听见了“驴、驴、驴”,突然就被自己逗笑了,松开了手里这头驴,翻身下来,拿过之前的白瓷小碗在眼前细细端详。
大暑天窝在南风馆的暖阁里,他身上憋得难受,心里也憋得慌。
一盏茶的时间已过,和祝独坐在圈椅上,挥着手往领口里灌风,想让自己好受一点,只是看牧蕴舟的眼神依旧不善。
他眼尾勾着红,不笑时,好看的眉眼冷淡异常,却又透着艳气,牧蕴舟被看得受不了:“你刚才把我按在那里时,我以为你看上我了,吓死了!”
“开个玩笑,真生气了啊?”牧蕴舟拿着装着饼金的檀木匣子过来,碰了碰和祝的手,作势要递给他:“要不,我哄哄你?”
见他不说话,牧蕴舟脸上兴味儿更深;“和祝,你刚才,不会是当真了吧?”“你怕我。”
他最后一句话说得肯定,和祝听得一怔。
说不怕是假的,但这话从对方嘴里这么肯定地说出来,他不由觉得心慌。
牧蕴舟这人,确实太过危险。
喜怒无常,看着被金银所缚,实则做事全凭喜好,和祝见过他认真时的模样,那种带着极具侵略性的气质,不是常在风月里打滚的人该有的模样,倒让他想起了另一个人,那种可怕的强势感,像是长期在权力中浸润出来的。
最重要的是,牧蕴舟对京城和皇家之事的了解程度,甚至远超过他。
他们俩并不是适合深聊交换彼此看法的人。
和祝情绪慢慢平复,只觉得嘴巴里的苦药味儿更重了,喝水也压不下去,他打开门,随手扯了个路过的小厮:“你去厨房给我要碗糖蒸酥酪。”
小厮应声正要去,身后的贵人突然又补了一声:“要再浇厚厚的一层蜜。”
小厮青玉身子一僵,红晕沿着脖颈一路蔓到耳根,连声音都在打颤:“是。”
和祝回身,牧蕴舟坐在他之前的椅子上,撑着下巴,表情完全放松下来,只眼尾微微上挑,仿佛见了什么有趣的东西。
和祝最烦他这样,走过去,纤白的指尖在白瓷碗壁上打了个转,蘸了点之前洒出来的苦药汁子,抹在他嘴唇上。
牧蕴舟下意识添了一口。
整个人都趴在扶手上干呕,俊朗的五官在和祝期待的目光里逐渐扭曲,皱成一团。
和祝舒服地喟叹一声。
爽快!
“我睡一会儿,等酥酪送来,你直接让他进来就行。”和祝打着哈欠,泪眼朦胧,倒在床上,不忘吩咐牧蕴舟,“把窗子打开。”
牧蕴舟坐在椅子上不动,嗤笑一声:“我说,就算这窗户对着园内,你也是真不怕我被人看见啊。大白天睡什么睡?”
和祝的声音越来越小,带着浓重的倦意:“就睡一小会儿,晚上还要入宫,得早些准备。”
之前一直假托水土不服,称病不宜面圣,暂居瑞王府养病。
后来宫里专门派了御医住在府中,早晨赵公公又来问,再推脱可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牧蕴舟有一搭没一搭接话:“你刚才就没想着,给我也来一碗?”
和祝没接话,房间里只剩下均匀的呼吸声,牧蕴舟这才发现他已经睡着了,他调整了个坐姿,眉眼低沉,胳膊懒散地搭在黄花梨扶手上,无聊地看着门外晃动的虚影。
之前的小厮青玉端着碗浇了蜜的糖蒸酥酪在门口踌躇,他紧捧酥酪,一路走来,指尖被碗壁烫得通红。
里面半天听不见一点动静,安静得仿佛没有人。
他好不容易鼓足勇气,轻轻叩门,没有回应,青玉咬着唇,打算再敲一次,里面突然有人声传来:“进来!”声音不大,若不刻意去听,很容易错过。
青玉推门而入,长桌后的圈椅上,正大拉拉坐着一个人,高大结实的身体只堪堪用一层轻纱掩着,长捷半敛,蜜色的皮肤和轮廓分明的五官,与楼中之人的纤弱窈窕截然不同,通身的气势强势得可怕。
青玉下意识关了门,愣在原地一动不敢动。
他还未挂牌,没受过调教,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眼前的人见他进来,也只是抬了抬眼皮,然后便无聊地移开了眼,仿佛他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青玉羞得脑中一片空白,耳尖红得要滴出血来,慌乱之中,才看见床上还躺着一人,翻身时衣衫散开一点,身上的皮肤白得晃眼,薄薄的一层肌肉附着在身上,流畅紧实,暖玉一般莹润透粉。
他试着走向床边,身后传来若有似无的笑声,转过头,半倚在圈椅里的人表情依旧冷淡,只眼睛里透着戏谑,像是在欣赏一出好戏。
青玉边走边看脸色,见那人没有阻止的意思,便大着胆子走过去,轻轻跪了下去。
床榻上躺着的,正是之前在廊道里拉着他的那个人。不同于身后之人的强势冷然,面前的这个人,眉眼如画,哪怕闭着眼睛,也是鲜活的。
他真好看!比旁边丹青序的牌首秋之还要好看得多!
怎么能拿贵人与秋之作比呢,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他连忙低下头,掩住心虚。
总是要挂牌的,不过是提前了一点罢了,其实、其实这样,也无不可。
羞耻和惶恐占满全身,安静的房间里,似乎只剩下贵人平缓的呼吸声。
绮念像干草遇烈火,一瞬间生长、膨胀,却又无处可去,只能被困在心脏里,发疯一样捶打着薄薄的皮肉。青玉的脸逐渐变得痴迷,清秀白净的面颊被激得通红,他提着一颗心,紧张地听着身后的动静,却又不受控制地扯下腰带,一点一点爬了过去,握上了那只干净好看的手,将那节葱白的指尖含进了嘴巴里。
温暖的、湿润的、滑腻的……
和祝从梦中惊醒,猛得起身抽回手,原本有些恹恹的桃花眼里满是慌乱,震惊地看着指尖上的一片水光。
他以前是住过男生宿舍的,别说是没腰带,就是光着膀子的男人也见多了!但就是这样,他还是被对方那含羞带怯的表情和豁出一切的架势震住了!
他惊慌地握住小厮的手腕,想将他从地上拉起来,对方却已经羞得根本听不进去他在说什么,和祝没防备,细白的脖颈被人一把搂住,地上的人看着他红润的嘴唇,突然凑了上去。
和祝当然不肯,又羞又恼,扭着小厮的腕子把人扔了回去,自己也从软榻上跌了下去。
他自幼习武,力气也比小厮大的多,见他还想挣扎,索性抬腿制住他的膝盖,将他的双手压在头顶,冲着牧蕴舟怒道:“你又发什么疯。”
牧蕴舟不以为然:“你觉得是我安排的?”
不然呢?
慢慢松开手,直起身子,楼里的小厮坐在地上哭得梨花带雨,整个身子都在抖,见牧蕴舟站起来,吓得直往和祝身后躲。
和祝手里安抚地摸着青玉的后颈,觉得牧蕴舟闹得过了:“你要是看我不顺眼就直说,何必为难别人呢?”
牧蕴舟这下真的被气笑了:“是你为难他还是我为难他?人是你要的,这也怪我?”
和祝没明白,地上揪着他衣摆的青玉确听懂了,好看的贵人初到莳花馆,不知道这里的规矩,误要了这碗浇了蜜的甜点。
蜜房羽客类芳心,冶叶倡条遍相识。
莳花馆,寻花带蜜。
京城声名最盛的南风馆,来这里的客人郎君们一个个儿心里想的都是花丛调蜜,面儿上却又偏要端出一副风流姿态,于是便有了这故作风雅的规矩。
客人看中的人若是到了年纪还未在楼中挂牌,便会点上一份浇了一层厚蜜的甜品,让所选之人手捧而来。
青玉知道是自己误会,白净的面皮从双颊到脖子红了个透,仰着头,掉着眼泪,小声地跟和祝解释。
和祝没说话,眼神在牧蕴舟和青玉之间流转。
牧蕴舟当时明明知道他误会了,却没有提醒,之后若不是得了他的允许,青玉也不会进来,摆明了是要看好戏。
不过这人向来随性惯了,他也没多指望过他。
地上的人一直在哭,越哭越伤心,和祝的手抚着他的脖子,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激烈跳动的脉搏。
自己这一误会,怕是对他影响大了。
和祝不会哄人,就往他手里塞了颗小金珠子:“你别害怕呀,我走时会让人把你带出去。”只是具体怎么安排还没想好。
牧蕴舟哧笑一声,嫌弃地打量了青玉几眼,性子一般,长得更一般,说好听点叫清秀,说难听点叫没劲。
他心里看不上,面儿上就更嫌弃了,哧笑一声:“喜欢这种白净的?”
这人,越搭理他他越来劲,和祝没接话,独自整理着衣袍往外走。
“诶,没到时间呢,去哪啊你?你这态度,是喜欢啊还是不喜欢?”牧蕴舟确实是有意纵容青玉靠近,是试探,也是好奇,他突然想知道,这玉一般的人,到底是个什么口味。
“回瑞王府,洗个澡收拾收拾啊,总不能宫里来接人,一路找到这儿吧。”
他开门的那一刻,牧蕴舟晃着手指,语气半真半假,玩笑似地开口道:“和祝,你今儿要真从这南风馆出发,保不齐宫里对你更放心呢。”
和祝身形一顿。
你知道个屁!
宫里的马车到瑞王府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瑞王世子拉着淳州来的弟弟,站在门口等候。
赵公公见状,躬着身子劝道:“还是让小公子一个人去吧。”他是皇帝身边的老人了,手里的拂尘一扫,嘴里说着拒绝的话,面儿上却全是恭敬。
钟离汋本来怕和祝一个人不自在,想陪着一起去,如今见赵公公这态度,便知道了陛下的意思,他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纸扇一合,点了下和祝,笑着跟赵公公打趣:“好啊,我就知道陛下偏心,平日里便觉得我没出息,现在和祝回来,连见都不想见我了。”
其实倒也没有很想去,陛下考问功课极苛,每次回来都得伤心好几日。
赵公公是皇帝身边的老人了,知道他是故意做给陛下的亲近,便拱手回道:“奴才定会将世子的这份思念转达给陛下。”
车轮声逐渐远去,车后挂着五排山形汉白玉挂串,钟离汋盯着这些摇晃的玉饰,有些琢磨不透陛下的态度。
陛下向来厚待荣王府,破例封了本朝唯一的异姓亲王,府中的器具衣饰,花纹式样,贵重又僭越,放在任何王公贵戚府上,怕都是万死难赎其罪。
如今荣王在淳州离世,陛下待和祝,只怕殊荣更甚。
可陛下的这份好,实在有些不留后路。
……
安泉地区的贪墨案牵连甚广,涉案人员现已查清,只是关于怎么处理,大臣们却争执不休。等和祝见到皇帝时,已是深夜。
“世子久等辛苦,陛下传您进去。”
他站在殿内,太监们悉数从两侧退出。
皇帝独坐在御案之后。
身后的楠木朱门被轻轻关上,小小的“咯噔”一声,磕得和祝心颤。
一瞬间,冷汗爬满了他的整个脊背,心脏藏在皮肉下疯狂跳动,他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血液在身体里流动,可是却没有温度,全身都冷得厉害。
这种从心底汹涌蔓延出来的可怕感觉叫做恐惧。
无论他如何努力说服自己,都无法掩盖来自内心深处的心虚和无助。
他爹破例被封为一字亲王,在淳州薨逝,却无人来报,既不合制更不合矩,如果有人拿这作筏子发难,他连辩解的余地都没有。
和祝只能赌。
倚仗的是赵公公的那句“小公子”。来了京城之后,他便只是荣王世子,赵公公是最谨慎的人,绝不会在称呼上犯这种错,他敢依循着在淳州时的叫法,定然是皇帝允许的。
“祝儿,过来。”低沉醇厚的声音透着亲昵,又带着上位者不容拒绝的强势。
和祝下意识握住了腕上的金花生,他想了想,没有称呼陛下,而是像在淳州时一样,软着嗓子道:“叔父。”
屋里的熏香闻起来闷闷的,熏得人脑袋发胀,隔着一张御案,对面坐着的人陌生得可怕。
只两年未见,他消瘦得让人难过,却远比在淳州时更像一个帝王,那种长期在权力中浸染出来的凛然气势,非但没有因为他身体的虚弱而削减分毫,反而凌厉得让人胆寒。
这个人,曾经也是真的视他如子侄,疼爱教导过他,他本以为自己已经被完全被惊惧所占据,却没想到,站在离帝王几步之远的地方,还会有近似近乡情怯和心虚胆怯的情绪将他困住。
四肢变得僵硬,他听到声音,几乎是本能地走了过去。
皇帝像是丝毫没有感觉到他的惧怕和疏远,硬拉过他的手,看了眼他掌心被金花生硌出来的红印,拿出帕子,细细擦拭他手心里的冷汗:“京城不好吗?”
天子脚下,富贵繁华。“……好。”
“好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回来!”
中气十足,吓了和祝一跳。
桌子拍得震天响,和祝闻着他身上那股若有似无的冷香,几不可微地叹了口气,别扭又笨拙地服软示弱:“别生气呀。”
果不其然,瞬间点燃皇帝的怒火,怒骂声像狂风暴雨一样袭来。
“我还心疼你们淳州苦寒,结果你们一个一个都住上瘾了是吧?我哪点对不起你们了,啊?”
“你胆子多大啊?水土不服,需要静养是吧?今天打哪来的?你才多大呀你就敢去鬼混?用不用明日就给你设宴相看?”
“我别生气?我怎么没直接气死呢?”
他越骂越生气,越生气声音越大,和祝觉得都是有身份的人,想着劝一劝别这样,结果气得皇帝直接抬脚踹他。
“我给你丢人了是吧?”
“不是,我哪敢……”对方完全处于不讲道理的状态,不管他说什么都可以被歪曲成另一重意思。
皇帝气上心头,将他与他爹和戎轮着骂,骂他爹时,便说那个狠心薄情之人,骂他的时候,就说,你这个小白眼狼!
和祝见他累了,适时送上杯茶水给他润润嗓子,没皮没脸地接话茬:“您消消气?晚膳时间早都过了,人都要饿死在这里了!”“那就是白眼狼也会饿吧。”
皇帝:……
皇帝被噎得无语,又踹了他一脚,末了还是喊了声:“赵全,传膳!”
和祝瞥了眼角落里的鎏金镂空香炉,里头燃着的紫茵香,与皇帝身上的冷香合在一起,会使人意志混乱。
这药,是他自己下的。
陛下待他如子侄。
可这样嬉笑怒骂,平常父子一般的相处方式,是他与他爹和戎之间的。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试图将自己活成另一个人。
晚膳时间已经过了,内御膳房早早得了命令,一直没敢懈怠,紫宸殿内一声吩咐,便有宫人将备好的膳食呈上来。
一张黑漆描金长桌,坐着皇帝与和祝两个人。
不说君臣有别,就是寻常人家,也极少会有长辈与小辈如此同坐。
进来的宫人们一个个眼观鼻、鼻观心,低头噤声,神色泰然,面对这不合规矩的一幕,谁也没露出半点异色。
虽然当时是为了岔开话题,不过和祝也确实饿了,热菜的香味蔓延开,完全遮住了鼻间那丝若有似无的冷香,也一点点驱走了他因恐惧而附着在四肢上的冰凉。
一种巨大的荒唐感油然而生。
在这种诡异的氛围里,和祝反倒安心下来,胃口大好,只觉得更饿了。
皇帝见他这副慢条斯理的样子,哼笑一声,挥手让布菜的太监退下,将远处的一盘百合糕推到他跟前:“别装了,今儿事务繁多,几个老臣纠缠不休,误了你的晚膳,老早就饿了吧,指不定心里怎么骂呢。”
“我必不敢。”和祝小声嘀咕。
黄釉瓷盘里盛着的,是他最爱吃的鱼糕。
新鲜的荆州青鱼,打成肉糜,加入上好的肥膘肉丁,蒸成晶莹洁白、香润嫩滑的鱼糕,再浇上一层特殊调制的汤汁,和祝挑了片入口,汤汁吸了半饱,鲜汤碰上绵软筋道的鱼糕,小时候在荣王府是这个味道,后来在淳州也是这个味道。
也是,淳州的厨子本就是从宫里拨出去的,味道自然不会有所不同。
他太知道皇帝想要他什么反应了。
和祝沉默半响,搁下手里的筷子,绷直的脊背垮了下来,认真地看着皇帝的眼睛:“我错了,我不该瞒着你,也不该不回来。”
皇帝神色缓了些,语气有些冷淡:“还有呢?”
“我不该当白眼儿狼。”
皇帝嘴角缓缓勾起勾起,拍了下他的肩膀:“胆大包天!也不知道像了谁,还真是头狼崽子!”
祝和别开身子,声音不大,却足够皇帝听见:“我都认错了你还骂我,以前也不知道谁一直教我男子汉要顶天立地,心胸宽广,现在又是谁揪着错处一直骂我!”
周围的宫人们倒吸一口冷气,将头埋得更低,布菜的小太监更是吓得“扑通”一下跪了下来。
殿内的气氛一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皇帝本已缓和下来的脸色变得更加冷淡,不悦地扫了眼地上跪着的人,赵公公心里一惊,连忙让人将他拖了出去。
“我说一句,你便有这么多句来顶。”
可不是一句吧。和祝这么想着,没把话说出口。
这个樱桃肉也做得好,他皱着眉没抬头:“父子哪有隔夜仇。”
“少吃点油腻的东西,当心晚上难受睡不着。”皇帝给他添了筷子虾仁,转头问赵公公:“长兴宫打扫出来了吗?”
和戎与皇帝相处多年,赵公公也算看着和祝长大,眼神里多了点犹豫:“回陛下,已经收拾好了,一应的用具和伺候的人都已经安排妥当,随时可以住人。”
“陛下、陛下若是留小公子在宫中常住,其实最近的裕和宫也空着。”
皇帝盯着他,许久没有说话,眼神晦暗让人发颤。
和祝筷子一滞,刚准备说话,耳边就传来皇帝平静的声音:“食不言。”
赵公公心中一寒,跪在地上,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能说出方才的一番话,已经是他的极限。
“你这是,另有安排?”
“老奴不敢。”他将头重重磕在地上,不敢起来。
“去吧。”
赵公公感激地一拜,然后起身,心里明白,轻轻揭过,也意味着没有下次。
长兴宫,是皇帝还是皇子的时候所居的寝宫,他登基后便一直空着,如今重新启用,太子会怎么想,其他皇子们会怎么想,朝中又会是什么风向。
是天大的殊荣,也是最难消受的皇恩。
皇帝将和祝当儿子养,活在一段幻想的关系里,骗自己和祝既是和戎的儿子,也是他的儿子。
他病态地在这段荒唐的亲情里寻求慰藉,又将和祝架在高处的悬崖之上,报复性地享受着这份扭曲的快感。
和祝坐在旁边,兴奋地手都在抖,这种游走在生死边缘、与一个疯子扮演父慈子孝、一步踏错都有可能激怒对方的感觉真是要把人刺激死了。
刺激过头的结果就是,睡不着。
夜深人静,心烦意乱,外界的一切刺激都被放大。
和祝眯着眼,屋里的描金缠枝烛灯好亮,树上的蝉鸣声好吵,风吹树叶哗哗哗、哗个屁啊。
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半点睡意没来,倒折腾出一身汗。
这下好了,更睡不着了。
他索性起身,穿着身单薄的寝衣,松了松领口,又将裤脚拉到小腿,捞了本志怪话本,借着室里微弱的灯光翻了起来。
天儿是热的,可书里的故事透着寒气。
说有些人若是走的突然,没好好跟骨肉亲人告别,就会产生执念,强行逗留在人间。他们为了逃避无常老爷的拘拿,就会找活人掩护,一般都是找邻居、朋友这些离自己家近的人,藏在他们的背后,借他们的阳气遮掩自己。
但是他们也怕啊,怕什么呢,怕跟着的这个活人突然转头,发现他们的存在,逝者若是对上生人的眼睛,这个遮掩的法子就不灵了,黑白无常就要来拿人啦。
所以这类鬼是藏在身后,见不得人的。
可是,好好的一个大活人,怎么也见不得人呢。
和祝翻着话本,半阖的窗框上,一道摇晃的虚影被雪雾似的月光拉得老长。
守夜的太监不至于睡得这么死,连个活人在殿外都发现不了。
估计是哪个宫里派来打探的人。
有人给宫里的消息安了双腿,他深夜从紫宸殿出来,一路上见到的所有宫女太监都已经知道,宫中住了位身份尴尬的世子,更不用隐在他们身后的那些人。
但是已经这么迫不及待了吗?
苦恼地合上话本,他睡不着,心里不痛快,便也不想让别人睡。
他轻着脚步,隐在窗边暗处,窗外人影浮动,有一瞬间影子落在他的脸上,暗色在眼前一闪,和祝打了个寒战,突然觉得身周凉飕飕的,连心跳都加快了几分。
若是以前,他会直接将人扔出去接着睡。
可今天不一样,今天是个刺激的日子,和祝睡不着,心里不痛快,便想跟别人分享一下这份感受。
若是好心将这人送回去,无论背后是谁,场面一定难看到让人终生难忘,今晚谁都别想睡。
这么一想,在影子再一次向窗边倾斜的时候,和祝在那人耳边打了个响指,在他震惊的目光中揪住了他的腰带,想直接将人提进来。
没提动。
和祝一连试了好几次都没提动,觉得自尊心受挫,脸色多少有点难看,外面的人也已经被拽的不耐烦了,顺着他的力道从窗外翻了进来,不着痕迹地推开了他的手。
这下外面守夜的人都醒了,一个个脸上都是担忧和惧怕,门一打开,守夜的太监们跪成一排:“三皇子!”
必然不是在叫他。
宫中有位皇子与他年龄相仿,只比他小一岁,想必就是他了。
想象中的场面竟然直接在长兴宫里发生了,且完全不难看,来人非凡没有一点被抓到后的狼狈和尴尬,反倒还气定神闲受了礼,挥手让其他人出去,沉稳内敛又透着一派矜贵。
和祝拉了张椅子坐下,冷眼打量着他袖口的云兽暗纹,用的是与衣服颜色一致的玄色丝线,只抬手间有微光流转。
恪州特供的重锦。
他打量着对方,对方也同样在观察他。
“你就是淳州来的那位哥哥?吓到你了?本来明日章平殿一同读书时就能见到,但我实在太好奇了,就想着先悄悄看一眼。你别跟我计较啊,不然明日父皇和母妃又该罚我了。”
恰到好处的语气,带着几分探究和好奇,又不显得咄咄逼人,配上那副干净秀俊的面容,在这怪异的时间和场合里,竟也显出几分诚恳。
和祝没有招呼的意思,对方也不觉得慢待,拖了张椅子坐在对面,上身微微前倾,借着昏暗的灯光,想要看清他的面容。
抬举了。这是真心话,但和祝觉得矫情没说出口。
他爹是异姓王,异姓王的意思就是,钟离汋那样的,才是他的堂哥,至于他,实在高攀了。
但是对方主动递话,他总不好实话实说,谁是你哥。
和祝站起身,端起一副斯文派头,行了个礼,腿上的话本啪嗒一下掉在脚边,刚准备说话,张嘴却打了个哈欠。
他瞬间反应过来闭上嘴巴,憋得两眼汪泪。
三皇子轻笑一声,放松下来,没了之前的拘谨,语气也轻快不少:“打扰了打扰了,今日实在太晚,我该走了,改天你若有空,我再来找你玩儿。”
和祝站着没说话,只觉得一股寒气正在慢慢渗进皮肤,蛇一样绕着他的小腿往上爬。
仿佛有什么东西从脚边的话本里爬了出来似的。
安静的房间里,只剩下蜡烛燃烧的噼啪声和三皇子的脚步声。
在三皇子的手触上门的那一瞬间,和祝终于没忍住叫住了他。
“怎么了?”钟离承玥转身看向他。
没怎么,看话本看怂了。
被吓到的和祝心虚地低下头,却看见小腿边摆着的一方冰鉴,心情瞬间有些复杂。
半晌,他缓缓抬起头,生硬地开口:“你想尝尝淳州的梨花酿吗?”
“我觉得我们确实有必要培养一下兄弟感情。”
和祝觉得丢人,一心只想着遮掩,嘴上说着胡话,以至于忽略了对方脸上一闪而过的浓重厌恶。
他只听见那个清亮的声音带着笑意说:
“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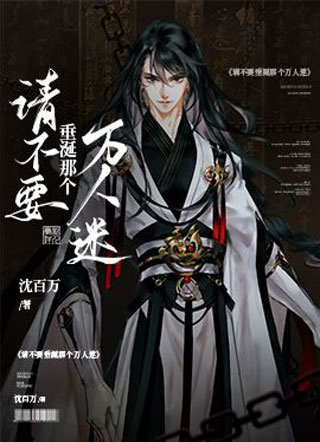
作者:沈百万类型: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