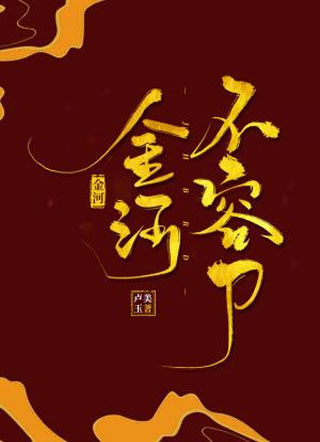
时间:2021-09-12 来源:长佩 分类:古代 作者:刑麻花 主角:伊勒德 付容
“杨文秀和萧程朗动手”,萧一仪放下茶盏,难得拔高了声调。付容“嗯”了声。他没有撑头摸脸,而是把手放在膝上,淡淡道:“似乎是撞上了杨文秀的轿子,那女人为难他们。”
付容跪在软垫上,视线一刻也不曾离开过萧一仪。后者却看也不看他,垂眸深思,指尖在杯盖上轻点着,问道:“萧程朗还带了人?”
“正一弟子,与他同行”,付容没了力气,干脆打算坐下,却被萧一仪眼神睨了回去,又摆正身子道:“他也没遮掩,直接报了名字,杨文秀是记起他来了。”
萧一仪叹了口气,“他许久未回神都,想必已经不清楚这当中风波。不过这样也好,萧程朗心思简单,叫他尝点苦头也未必是坏事。”
付容见萧一仪若有所思,并不急着插嘴,片刻后听她道:“杨成被贬常州也有一年多了,杨文秀定然坐不住。”
“神都开放后更是鱼龙混杂,我们要想防着杨成,难。”萧一仪顿了顿,话锋一转,“萧程朗上正一后你再没见过,竟也能认得出来”,她抬手抚上太阳穴,语气中似有埋怨,“重中之重却放不进心里。”
付容垂眸。
萧一仪拿起茶杯,细细品了品,摇头道:“喝过了姑姑宫里的东西,再来你这猪窝驴舍,吃什么都难下咽了。”
金玉其外的付小侯爷却没点反应,“阿姊,再不起要犯病了。”
“好说”,萧一仪终于看向付容,瞥了眼门外,没瞧见人后才淡淡道:“你们倒是会过日子。谢仁满城追杀刺客,你把人带回来玩金屋藏娇。”
付容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低下头干巴巴道:“我错了。”
他道歉只会这一句,语调还不是认错的态度。萧一仪听了十余年,听得耳朵都快起茧了,抬手揉揉眉心,“我问你,今日上朝,可是谢仁先刁难的?”
“他也敢?”付容晃晃悠悠地站起身。可他根本没跪多久,却断了腿似的要往萧一仪身旁的椅子爬去。菩萨心肠的长小姐立刻抬手捞起他,把人送进了面前的椅子上。
“他若是有这胆子,我杀人后便立刻告状去了”,付容刚一坐下,浑身的骨头便全散了,拢了拢大氅,哑声道:“是柳长风和杨东桓。”
萧一仪蹙着眉道:“柳长风?这事同他也有干系……他是如何说的?”
见付容不适地皱起眉头,萧一仪赶忙道:“罢了,我能猜到。柳长风恨透了你,自然说不出什么好话来。”
她拉过付容的手,指尖搭在他手腕上,感受到那人剧烈跳动的脉搏,头也不抬道:“春池,唤人备晚饭吧。”
等春池离开后,萧一仪才放下手,见付容眉间尽是倦色,忍不住感慨道:“北境路途遥远,快马加鞭也要近四日的功夫,我想……”
“阿姊”,付容抬起头。他额角刘海儿已被冷汗打湿,盯着萧一仪,一字一句道:“是我去北境,同你没有干系。”
萧一仪点头,“自然了,可谁让我今日惹恼了尊后”,她虚起双目,身子前倾,“付金,别再动些歪念头。我说过会治好你,阎王便不敢早收了你去。”
她按住付容手腕,“我费这么大劲,不是吃饱了撑的”。后者想要挣扎,却使不上劲儿,只能咬牙,死死盯着她看。
萧一仪突然笑了,“还是说,你打算带着宝贝奴才,一起躲去北境快活?”
付容忍不住喊出声,“阿姊!”
他面若寒霜,冻得牙齿咯咯作响。萧一仪拍拍胸脯,“这么凶,阿姊日后不再说就是。不过那胡人……”
付容自然不是同她发火,听到这话脸色缓和不少,却还是有些郁气。他见萧一仪摇了摇头,并无反应,抿唇不语。
“为何不肯?他在台上那般桀骜,偏生到了你这儿乖顺可人。阿容,这是神都,他绝不干净。”萧一仪表情只一瞬便冷了下来,宛若名刀出鞘,锐利异常。
付容道:“没什么理由,瞧着顺眼罢了。”
萧一仪一滞,竟然反驳不得,见付容揶揄目光,骂道:“说正事。”
“不干净我也认了”,付容撑起身,春池站在门外,福身唤道:“小姐,侯爷,晚膳备好了。”
付容没个站相,身子骨软绵,冲春池淡淡道:“阿姊不让我收下人,春池,你得好好劝劝她。”
春池闹了个大红脸,萧一仪却怒了,“他也配与春池相提并论,你莫不是失心疯了。”
她站起身,语气沉重,“你还是放不下他。外人都清楚你对他的心思,多少痴人要往你身上扑。付容,旁的也就罢了,若是你身边多了个隐患,我如何能安心?”
“左荆河已死,大周再无清河王。世上千千万万个左荆河,不论再像都不是他。付金,别再执迷不悟,这话我同你说了十年,我也不想再说与你听了。”
付容没有反应,并不回答身后的萧一仪。他抬脚跨过门槛,转身便瞧见了门边的伊勒德。
男人站在长廊里,靠墙抱胸,待见到付容后便立刻直起身子,道:“他们带我看了院子。”
“如何?”付容抬眼,面色苍白,说话也有气无力。伊勒德有些怔愣,半晌沉声道:“离你远了些。”
他长发高束,眸中藏着几不可查的炽热,视线锁定着付容,侵略性十足。伊勒德走近了些,微微低头,垂眸看着付容卷翘的睫毛,“住你院子里。”
付容蹙起眉头,正欲开口,便听身后一道声音响起,语气不善:“侯府可不是什么野猫野狗都能进的。”
萧一仪说着,从屋内踏了出来,上前挽住了付容的手臂。她身量高,与付容站在一起,端的是郎才女貌。
“阿容耳根子软”,萧一仪踮起脚尖,竟在付容耳边吹了口气,惹得他偏过头,表情难看。萧一仪却不以为意,笑道:“人须得有自知之明,若是他舍不得说,我便来做这个恶人。”
她站定身子,伸出左手,伊勒德尚未看清,一直站在远处角落的春池便突然闪身出现在他面前。她伸出手,掌心成爪,来势汹汹。付容见此,刚想出声,却被萧一仪攥住了手腕。他扭头,后者脸上写满了坚决,不可撼动。付容回过神,望进萧一仪如墨的瞳孔中,又想到自己的失态,顿时说不出话来。
伊勒德依旧没有动,春池眸光一闪,电光火石间收回了手,抬腿翻身直接朝男人脸上踹去,动作快到来不及捕捉。她鞋尖出陡然冒出把刺刀,眼看逐渐逼近男人脸颊,他却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任由那冷锋袭过来。
“春池。”
千钧一发之际,春池停了下来,那刀尖正好抵在伊勒德脖颈上,差一毫便能要了他性命。付容见此,第一反应竟是松了口气。
“不会再有下次。滚得越远越好,别让我看见你”,萧一仪松开付容,冷着脸甩手离开了。春池看也不看伊勒德,收回腿,搀着萧一仪走了。
付容没有心思跟上去。他闭眼深吸一气,半晌才开口道:“侯府中的规矩,你不大省得。”
伊勒德摇头,又意识到他看不见,道:“我会学。”
“只需一条”,付容睁开眼,额头冷汗连连,语气嘶哑,“听话些,本侯讨厌意外。”
付容没有多留,抬脚便往前走。伊勒德不得不后退闪身,为他让出路来。
他看着付容的背影穿过曲折回廊,踉跄上前,见自己的影子与那人身后的波浪交缠不休,呼吸一滞,停住了脚步。等他再看,付容早便消失不见,幽静的庭中只剩下他自己。
伊勒德张了张嘴,手中滑落出一条锦带,最后掉在了地上,是绣着芙蓉花的深金色香包。
天成了灰色,怎么还有影子。伊勒德抬头往外看去,原是夜色催更,月亮已出来了。他就站在原地,并未看见,远处的付容不知何时站在木柱之后,良久,抬腿离开了。
付容侧脸被月光映的洁白,墙角内本虫鸣阵阵,他经过时却倏地歇了。付容抿唇,脚步愈来愈快,可还未走出回廊便停了下来。他咬牙,却怎么也不肯转身,干脆抬脚踢在了一旁的木栏上。
付容想起当年在国子监,想到那人即使跪在地上,也是一身风华,如何都盖不住。
为什么偏偏是那胡人像他。付容痛苦地闭上眼睛,只要再多想半分,心脏便要疼地炸裂开来。他赶忙往前走,脚步浮乱,几乎是落荒而逃。
那又怎样呢?左荆河死了。死在昭和四十八年那个冬天里,死在无边无际的冷夜中,一个人埋在了数千尺深的冻土之下。无人知晓,无人纪念。评书写他是“惊才绝艳,百年难寻”的英雄人物,可到头来,大周再没有一个人提起他。
付容终于走不动了。他扶着木桩,忍不住干呕起来,摔在了地上。他背靠着桩子,任由明亮的月光照到身上,将浑身脆弱映得清晰可见,也没有再动一下。
他知道,自左荆河死在那天寒地冻的别院里,他最后的救命稻草便被生生斩断了。付容想要忘记了,可事实上,他根本记不得左荆河的样子。
他只有抱着仅剩的一些回忆过活。左荆河永远不会知道,那些微不足道的话语动作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
付容摇摇晃晃站起身,方才的迷惘仿佛从未存在过,他又变成了那个不可一世的小侯爷。
萧一仪说错了,他比任何人都想活着。他要活,要争一口气,要把这世道变成臭不可闻的泥塘,要让左荆河后悔如此狠心,如此绝情,如此离开他。
付容扶着柱子往前走。他一步步地向前,再也没有回头看一眼。远处的天边隐有轰鸣,付容虚了虚眼睛,豆大的水珠砸到了地面,发出清脆的嘭啪声。他继续向前,那“雨点”声却越来越响,他烦躁地抬手一抹眼角,加快脚步。
想活下去,可似乎已没有办法了。
春池匆忙推开门,进屋后又意识到自己失态,小心翼翼地关上门,却发觉萧一仪没有反应。她走近了些,小声感慨道:“真是奇了怪了,都打了好一会儿的雷,还不下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