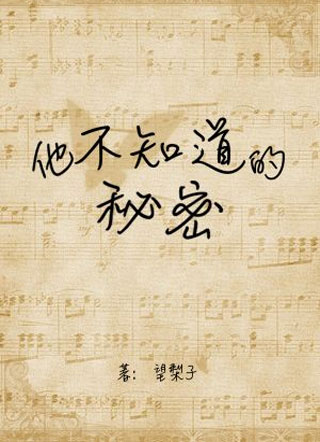
时间:2023-12-01 来源:寒武纪年 分类:现代 作者:望梨子 主角:陆海时 舒博云
就像这样,我联系上舒博云后就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络,每到周末他就会如常带我去那家TempoBrew吃饭,跟舒博云吃饭的好处就是安静,他不会和有些人一样问东问西,也不会像我其他几个朋友那样叽叽喳喳地边吃边吐槽今天哪个教授又拖堂了多长时间,又批斗他的画作如何如何。
“丁老头说抓只蛇沾点颜料放画布上让它自己扭,成品都比我画的有艺术感!我!他!他这是在诋毁我的人格!践踏我的自尊!”南凃嘴都气歪了,只穿着裤衩在宿舍里大吼大叫,声称与丁老头势不两立老死不相往来。
丁老头是我们专业以严格出名的老教授,他以严格的教学风格而蜚声校园,所以但凡是的课堂,就没人敢翘课,丁老头喜爱的作品大多是写实主义,追求真实,通过画笔还原出最真切的物象就是他毕生所求。
南凃追求的是简约线条,极致色彩,嗯……但我认为,他交上去的作品里肯定有和丁老头故意作对的情绪。
最近要准备学校的艺术节了,大家心情烦躁点都能理解。
“你是要人格自尊还是要学分?毕业就和他没瓜葛了,还有一年了再忍忍。”我没什么诚意的安慰道,看了看时间,四点半,该收拾收拾去找舒博云吃饭了。
“哈,陆海时!感情他骂的不是你!我看他就是不欣赏我的抽象流派!”他抓了抓头发又松开,爆炸头越来越炸,跟他整个人一样。
“哥哥,你也不想因为得罪丁老头拿不到成绩导致没法毕业吧?”我们寝室的留学生亚历山大说。
真受不了了,到底是谁教他的中文?
“咱们仨里面压力最小的就是亚历山大,凭什么?凭什么他亚历山大压力最小?”
亚历山大不是油画系的,自然不懂美术生的痛苦和丁老头的恐怖之处,也正常。南凃开始乱开炮,简直要被他逗死了,我又看了看时间,再跟他们墨迹下去就迟到了,南凃却堵在门口不挪坑。
“起开,我要出门了。”我站在南凃面前。
“去哪?”南凃打量了我一下。
“吃饭啊。”莫名其妙,这个点出去还能去哪。
“妹子?”他又问。
“男的啊。”这家伙……不会要跟来吧?
“不信,如果真的是男的,你不会加一个‘啊’字,你在故作轻松,你在伪装。”他胸有成竹道,仿佛自己是看穿了一切的侦探。
“爱信不信!”我无语。
“吃什么啊,给我带份!”亚历山大从上铺探出脑袋。
“带不了,我回来很晚了。”我把南凃扒到一边,赶紧趁机会出门。
“还说不是妹子?有本事今晚你别回来了!”南凃在宿舍楼道恶狠狠道,搞得好几个人频频回头看我,这怨妇似的家伙,他不丢脸我还丢脸。
说到这事,我有点好奇舒博云住在哪个宿舍,怎么大学三年都没遇见过他一次?这也未免太不赶巧了吧?所以当天晚上跟他吃饭的时候就问了,他告诉我,他不住学校。
“家近。”他吸了吸鼻子,回答道。
这天他依然点了他的特浓咖啡,我忍不住开口问他,今天也需要熬夜吗,他默不作声地点点头。
“你感冒了?”刚说出口,我便想起小学他一到冬天就用一堆卫生纸的事情。
舒博云说他有鼻炎,一到这个季节就这样,所以出去都不敢吃太烫的东西,不然鼻涕会狂流不止,便随身带好几包纸巾。
他擤的鼻子通红,店内暖黄色的灯光下显得他脸色怪怪的。
这几天学校有点忙,我这几天也天天晚睡,因为要赶下次艺术节的画,这几天刚给老师看完稿子,丁老头没怎么为难我就给我过了,反观抓耳挠腮的南凃,我算个幸运儿。
我问舒博云艺术节会不会演出,他点头,然后拿出手机放给我听他录的demo,据说是他们编曲专业的同学作曲后,他再弹出来的。
他的琴声感情很丰富,连我这个不懂欣赏音乐的人都能听得出来他的优秀。
“和他们合作的。”舒博云指艺术节的节目。
“很好听啊,你们跨专业还能合作?哦,我们也有合作,就是大家一起画一张大点的画而已……说是大一点,也有三十米长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因为意见不合吵得鸡飞狗跳的。”想到这个,我的头又开始疼了,今年的主题还没定下来呢。
我不想跟他说糟心事儿,就捡点其他的话题抛给他:“你们到时候几点开演,我会去听的。所以你最近都是因为这个熬夜?”
舒博云今天没吃多少东西,吃了几口就把叉子放下了,他又从大衣口袋里摸出眼镜盒,把眼镜片擦拭干净再戴上。
他眼睛很好看,眼尾微微上挑,戴上眼镜后眼神里少了平时那朦胧的迷茫,显得有些犀利,他本来就有着侵略性十足的五官,再加上他平时没什么表情,更让人难以靠近他了。
但他说话不刻薄,相反慢吞吞地,也没太多长句子,是个懒得动嘴皮子的人。
“算是吧。”他喝了一口咖啡,接着问我:“我去看了画。你画的是谁?”
我一听,他肯定是去B20的楼底下看画了,那张画太显眼了:“寝室的同学,我们经常互相抓对方当自己模特的,一个叫亚历山大的留学生。”
“画的很逼真。”舒博云点评道。
“丁老头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说要挂B20楼梯口的主意也是他提的。
“丁老头?”
“我们系的老教授,下次艺术节指给你看,他今年开幕式要登台讲几句话。”
舒博云点点头,还想开口说些什么,可又不说了,我每次都要被他欲言又止的举动挠得心痒痒,或许是因为小时候的热情过剩给我留下了教训,怕又把他吓到,我依然保持尊重他的态度,还是不要多嘴的好。
虽然我已经在意到注意力无法集中了。
回宿舍的路上我试图把好奇心按下去,便问他:“你以前就学钢琴吗?从小学?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会弹了?”
“会。”他回答的言简意赅。
“那你父母从小就培养你当钢琴家?”我裹紧外套,把手插进兜里。
“……嗯。”他回答的很犹豫。
“你叫舒博云,这个名字不会灵感来源于舒伯特吧……”
“那你为什么叫陆海时?”
“因为我爸妈从来没见过海,你也知道我老家那个地方,除了田就是山就是河的,就是没有海,所以就叫这个名字了。”
舒博云的眼镜起了一层白雾,围巾裹住的半张脸下可能是用鼻子笑了下,我纳闷这有什么好笑的,这人笑点还蛮奇怪。
我临着门禁前到了宿舍,南凃这家伙一脸幽怨地望着我,我以为他又要开始死缠烂打,开始拷问今晚到底去干了什么。
但我看亚历山大坐在椅子上,盯着电脑打开的PS,也是一副苦哈哈的表情。
“这都怎么了?”
就出去吃个饭的工夫,怎么就成这样了?我疑惑地拉了个凳子,坐在亚历山大旁边。
“今年艺术节那个合作的大板子,丁老头说,主题要我想一个打个草稿明天下周五交给他,他到底是几个意思啊?”
我一愣:“不挺好的吗这不正代表他开始欣赏你的审美了啊。他都放心把这么重要的主题交给你了,那还不证明你的艺术其实已经打动他了?到时候可是全省多少千多少万的人来看你的奇思妙想啊!”我转过头,问亚历山大:“那你又是怎么了?”
“今年海报,我做。”亚历山大现在也压力山大了。他声称一定是南凃的诅咒让他变得不幸。
我坚信,我们宿舍今年撞大运了,要知道一个专业一百来人,大学就四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还想安慰他们几句,南凃和亚历山大却一转攻势,马上开始问我晚上到底干什么了。
“我真的跟朋友出去吃饭了啊。”
“谁啊?”
“就是咱们学校的,跟你说了也不知道。”
“那你说,叫什么名字?”
“舒博云。”我心思,说个名字他就能知道了?
“舒博云?卧槽。”南凃忽然变了表情:“他是你朋友?”
我一怔,心说南凃难道知道舒博云,就问:“你认识他?就是咱们音乐系的——去年还弹钢琴了来着,要不是他登台,我还真不知道他在这个学校呢。”
南凃的表情告诉我,他认识舒博云,而且对舒博云的评价不怎么好。南凃虽然平时贱贱地,有点事情都要跟大家吐槽吐槽,但只对事不对人,即便跟人吵架,也是吵完就完事儿了,从来没有隔夜仇,所以人缘一直很好。
可他怎么会认识舒博云?我想到南凃是本地人,便猜:“你俩不会是一个高中的吧?”
南凃的眼神满是不敢置信,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反问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因为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时也不太熟,他就来了一年,然后……”
“他有问题,真的。”他打断我。“你最好离他远点。”
洛城艺术大学每年春季都会举办一次全省规模的艺术节。艺术节表演的主会场在校内的大礼堂内,各类艺术表演和演奏都将在这里轮番上演,我们创造型专业的作品将会在学校建筑内各处展出,在大学主楼的一楼有一个大展览室,油画作品都会在这里展出。
南凃犯愁的合作作品,是三十米长的艺术版画,每个学生都会负责一部分的画作拼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利用室外的场地做展览。
他熬了一个星期的夜,拿出五个不同的稿子让丁老头选一个,他说他接受不了想破头皮想了一个星期的灵感被他全盘否决,所以决定量产,供丁老头任意选择,总之就是不要每天逼着他改稿子就好了。
最后丁老头没为难他,真的从这五个其中敲定下一个方案,南凃简直欣喜若狂,在寝室里跟中举的范进一样。
“你是对的。”亚历山大哪怕自己都焦头烂额了,也乐呵呵地给他竖起大拇指。“用一个成语来说就是‘未雨绸缪’。”
“亚历山大,你还是担心下自己吧,你今天再搞不出来排版,小心变成第二个南凃。”我出门前嘱咐他。
我试图让自己忙碌起来,将南凃上次对我的叮嘱抛之脑后,但他越是这么说,我越是好奇。因为南凃并不打算告诉我为什么会这么说,他在不偷偷嚼人舌根这一点上贯彻到了极致。
只是一再叮嘱我:“吃个饭得了,别深交。”
舒博云又不是吃人的老虎,也不是什么危险的杀手,他性格挺温和的,脾气也挺好的,根本没他说的那么严重。我不知道南凃是怎么看舒博云的,也不知道他们曾经有什么瓜葛,看一个人的好坏,我自然有天平衡量,不会因为其他人的一言两语有所动摇。
我安慰他道,我有数,南凃狐疑地看了看我:“那就行。”
他有时候可真像个老妈子。
舒博云小学的时候也很好,俗话不是说三岁看人老来着?除了他不太爱搭理人之外,哪哪都挺好的不骂人不打架,不扯女生辫子也不拖男生裤子……问他借东西都是百分百成功率,虽说我有时候也看不惯他,但有这么个同桌,虽然也就一年的时间,也让我度过了比较愉快的小学时光。
我抱着画具去画室,打算先画他个四五小时再说,今年艺术节的主题色是翠绿,我打算画些花草树木为题材的作品,在画室翻了一堆植物写生,这一部分是我最不擅长的——一直都在画人物,是时候跳出舒适圈了。
我想到对植物有些了解的舒博云,拿出手机给他发了消息。
‘你养植物吗?’
‘养。’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植物?’
‘你要养?’
‘不是,是画,今年艺术节的主题色不是翠绿吗,我就想画点植物相关的。’
‘你在学校。吃饭吗?’
这人怎么动不动就吃饭?我把聊天记录往上翻,翻了好几页都是:吃饭?go。吃饭?老地方。吃饭?吃。……
我看了眼画布上画的一堆植物练习,看着看着还真有点饿了,莫名其妙的……然后我就跟他随便约了个食堂,下午三点食堂都没什么人了,正好先吃个饭吧。
舒博云早就到了食堂,他坐在那里我就能一眼看到。
我屁股刚挨凳子,还没坐热乎呢,他就开口说:“你要植物吗,我家有,你可以照着画。”
我理解的意思是,他要把家里的植物特意搬到学校来,就摇摇头拒绝了:“那多麻烦你,我看看这次能不能从艺术节拨给画室的经费里出,去买一盆算了。”
舒博云停顿了下,点点头。
我以为他就是客套客套,就赶紧去点了饭回来,饿的我前胸贴肚皮了。
我吃着饭,他却还是坐在面前,戴着眼镜,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你不吃吗?”
“吃过了。”
啊?那他叫我来吃饭是做什么?我瞪着眼睛把嘴里的面条咽下去后弱弱地说:“我还以为你没吃所以顺便叫我来吃饭呢……”
不对,不对,重点肯定不是在吃饭,我把脑子里的那几句聊天记录又倒带了一遍,难道他是因为听我问他植物的事情,他就是为这事跟我提的吃饭?然后把我叫来,告诉我他有现成的可以借给我画?
刚才被饥饿控制住了心神,仔细一想,这个猜测简直不要太合理。
我心领神会,“你家都有什么植物,如果有合适的话,我想借一盆,就不用再麻烦去申请现买了。”
舒博云看起来在走神,他好一会才抬眼看着我说:“你想要什么?”
被他这么一问,我还真有点迷茫,看了一上午的植物图鉴,还是没决定下来具体的植物。
我吃完最后一口,沉吟了一会儿:“你带我去的那家店,店门口不是有一盆……绿萝?我看那个挺好的……”
那盆绿萝筐子也很好看呢,是竹子编的竹篮,就是最近都没见过那盆绿萝了。
“知道了。”
“你真的要搬来学校吗?不麻烦吗?”
“不麻烦。”舒博云低头摸着手机,像是在给谁发消息,然后他抬头:“搬到哪里?我直接拿过去。”
我没拒绝他的好意:“你知道油画专业的E10号楼五楼的画室吗?5001画室。到时候我在楼底下等你吧?怕你找不到地方。”
他告诉我明天就可以带来,这可真是解了我燃眉之急,心说舒博云这人还怪好的,根本没有小时候那么不近人情,也就完全否定了南凃的‘警告’,都怪他大惊小怪的。
舒博云第二天如约而至,提着一盆绿萝在E10楼的楼底下,好多路过的人经过都忍不住看他。
“他们为什么看我?”舒博云把那盆绿萝递给我。
“看你好看呗。”我打趣他道。
舒博云不讲话了,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就当他是害羞了,低头去看那盆绿萝,可这绿萝怎么有点眼熟?花盆好像那天我在TempoBrew看到的……竹篮,我把心中疑惑说出口,只听舒博云坦荡说道。
“就是那盆。”
我从疑惑到惊讶,再到站在原地迟迟挪不动脚步,我用一种诡异的目光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这盆绿萝。他突然驻足转身回望我,我又抬头看着他波澜无惊的样子。
啊?
他不会是把人家餐厅的植物顺来了吧!
或许南凃说的是对的,我真的该听他的话,难道真如他所说,舒博云莫非真的不太正常?就因为我说那个绿萝挺好的?所以他就?啊,我的天啊,我该用一种什么表情面对他,我该怎么办啊?说到底,罪魁祸首还是我啊,我要是不提那盆绿萝,他会不会就不去偷了,打住,我在想什么!我怎么可以就给人家直接宣判死刑呢!
在短短的一秒内,我已经想好了几百种反应,没有任何一种能让这种奇怪的气氛缓和下来!我该装傻打个哈哈吗?还是该告诉他偷人家东西是不对的?啊啊怎么想也不对吧!哪种反应都无法扭转目前的局面啊!
在我头脑风暴的时候,舒博云大概是看我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青的,走到我面前,板着一张脸开口说:“你怎么了?”
这句话我听过,和电影中路人甲识破伪装成普通人的杀手时说出来的一模一样!
“没,没怎么。”我咽了口唾沫,忽然发现艺术果然来自于生活,要是我,我也会和路人甲说出这句状若一切无事发生的台词。
舒博云皱起眉头来,我第一次看他露出这种表情。
“你不会觉得这是我擅自从店里拿来的吧?”
啊,我的老天爷啊,我在心里默念了三次我的老天爷啊。其实我猜得更恶劣,我以为你是去当小偷了!好吧意思都差不多!
“这本来就是我养的,你在想什么?”
他第一次说这么长的话,我有些不太适应:“啊,这本来就是你养的。”我重复他的话。
舒博云自顾自地往前走,我赶紧跟上问:“这是你养的?那怎么会在那家店放着啊?”
“那家店是我叔叔开的,店里的植物,都是我养的,放在店里当摆设而已。”
啊?叔叔?那个头发花白的大叔是他叔叔啊,怪年轻的怎么就头发全白了……
哦,是亲戚啊……
我赶紧哈哈两声掩饰尴尬,背后冷汗都冒起来了,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南凃这个混球,要不是他那天对我的警告,我怎么可能会想到这里,果然不能听他的危言耸听。
我问舒博云,怎么后来去都没见到这盆绿萝,舒博云告诉我天气太冷,放回室内挂着了。
“你喜欢养植物?都养什么?”
“什么都养。”
“它怕冷吗?”我指了指这盆绿萝
“有点,画室冷吗?”
“晚上挺冷的,要不我晚上带回宿舍吧?”
舒博云说都行,他进来看了眼画室,没多逗留便走了,而我盯了一下午的绿萝,晚上还是决定搬回宿舍,万一把它冻死就不好了。
南凃这家伙还问我这盆绿萝的来头,他还敢问,我气不打一处来,赶紧把今天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通,没想到他反应有些出乎我意料。
“不是,我也不是那意思啊!”
“你没那个意思,那你说人家有问题干嘛!你真是!”
“卧槽,冤枉啊大人,我说的有问题不是指他是小偷啊!”
“那你什么意思?”
南凃又当哑巴不回答,我就知道,关键时刻啥也不说,气得我把绿萝从他手里夺走了。
“别生气嘛,要不咱俩合作一下,我也画画绿萝?申请今年作品摆你旁边……”
“拒绝。我要去申请一个离你作品最远的位置。”
这一个月寝室的人都忙的不可开交,亚历山大天天扎根在电脑面前练习如何年纪轻轻就当驼背,我经过他后面的时候就给他后背来一巴掌。
他还不领情,以为我打他,我说这是中华传统,每个家庭的小孩儿都要经历的,这是在给你体验本国传统文化,他一脸狐疑仿佛不相信,我说你不信问南凃啊,南凃小鸡啄米地点头。
而南凃就天天在群里问大家的进度如何如何,每星期都集合看一次,以免有的人不能及时完成上交,我说你这个领导当的还挺称职,他就一脸不屑:南哥不轻易出手的。你看着吧。
前几个周我以太忙为由拒绝了舒博云的‘吃饭’邀请,这星期好不容易空下来,我给他发了消息,他回的很快,这周五依然去老地方吃。
我进门后,那个白头发大叔就冲我笑的意味深长,我估摸着是舒博云告诉了他关于我的事情。
“你们俩很久没来了啊,学校很忙嘛?”白头发大叔问。
我颇为惊讶,原来我没来的这段时间,舒博云也没有来啊。
“快要艺术节了,到时候叔叔也来看看?”我说。
“每年我都去的,今年更要去了。”他还是笑着说,然后看了看舒博云。
虽然我不知道今年更要来的理由是什么,也还是应和着笑了笑,我回头一看,舒博云站在我身后一言不发地,今天一见到他就感觉他不太高兴,真的,我总感觉他有时候突然就不高兴了,但我又完全搞不明白他到底哪里不高兴,让我也挺郁闷的。
他没吭声,也没跟他大叔打招呼,就自己往里走了,我看了眼白头发大叔,他好像见怪不怪了一样,根本没在意,催我也赶紧进去坐。
起初我以为是这几周没跟他吃饭他不高兴了,但也不太可能就因为这个生气了吧?他答应吃饭的时候可是很爽快的。
真是奇了怪了。
“最近练习忙吗?”我把外套脱下来,边问他:“你弹得怎么样了?”
舒博云盯着菜单不讲话,我又叫了他好几次,用手在他眼前晃了晃,他才看向我。他今天没戴眼镜,眼睛像是蒙了曾雾气一样,眼球来回转动着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