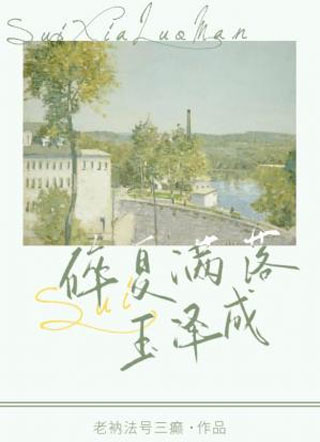
时间:2022-08-05 来源:长佩 分类:现代 作者:老衲法号三癫 主角:余还来 玉泽成
说是爬山,其实也不过是市内的一个小土坡,大几十米一百出头的高度。不过就算这样,对我这个上了年纪(对于刚入大学的学弟妹们,我的确是个老人了。)又常年不爱动弹的人来说,也依旧够我喝上一壶。
还有几个人,那会儿我也都不认识,猜想都是泽成的朋友吧,因为他们身上的气息也都和泽成有些相像,运动的,阳光的。
那会儿山路还没翻修,通往山头的石梯蜿蜒曲折而上,张牙舞爪地摆在我脸前。我看出了山的嘲讽,心里气不过,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也不能弱了气势。接了泽成递过来的水就一马当先冲了出去。
泽成瞧见,暗笑了一声便跟在我后面。
我算是这几个人个子最矮的那一个,不过两条腿蹬的频率倒快,小鸡啄米一步一步竟也爬了上去,未曾掉队。其间他们三两说笑,悠闲得很。我是全无力气,大汗淋漓,断断做不出轻松的样子。泽成一直没加入他们的交谈,只偶尔应两声,一直跟在我后面。后来我问泽成,他只说他盯着我的屁股爬了一路,半点沿途风景都看不见,全被挡住。我自己检讨并不算胖,后来才明白过来,是有人心猿意马,眼里落不进别的东西。
爬至山腰,正好有个供人休息的点。他们倒想一鼓作气,赶个早能看个夕阳。然而泽成却直接说自己累得很了,口渴的紧,要歇息一会儿,引得旁人都在取笑他。索性一起坐下来开始畅谈,一时间欢声笑语。我倒乐得如此,气氛轻松自在,坐在一旁听着他们吹吹牛逼,互相开开玩笑,吹着风也挺开心。泽成这时候买了水回来,每个人都有。山上的水贵,我自然是舍不得。我本不想让他又欠个情,于是便要找了零给他。
泽成笑着回绝,说:“下次你再请回来就是了。”
爬山前他给我的早就喝完了,嗓子早就冒烟,我也没多推诿就一口灌了进去。水很清洌,大概是被冰过的,也甜得很。
泽成就在一旁看着我,他一双眸子看着我的眼神直发烫。泽成本就生得好看,极其英气,这么看得我更是不自在。
“怎么了么?”我摸了摸脸。
“没什么。”
一行人到了山顶,刚好晚霞漫天,如同水粉一样涂抹在整片星穹。有人带了相机,我们一行人就当着这景,托了旁人给我们照一张。后面泽成说,要和我单独照一张,我也没想就应了。后来他特地找了那张照片洗出来,镶了框置于我们的床头,一直在那里。大抵是想一直睡在那天的晚霞里,我也是。
烈烈晚霞如火烧破天,醉了地上的两人成双。
其余人都已走散,泽成突然定下来,深吸了口气说了我永远忘不了的话。
“阿来,我爱上你了。”
泽成从来不拐弯抹角,他本人就是这样赤诚而热烈。每每我问起他当时为何会突然说这样的话,明明我们也才认识不算很久。他总是眼睛里缀着点点霞光,笑着说:“晚霞醉人,我也一定是昏了头脑。但我要不说,那会是我一辈子的憾事。”可总是不说为何而爱,从何爱起。
直到很久之后,我们重回故地,又遇见了像当年一样那么好的晚霞,泽成终于说起,就是那日新年夜,我俩一撞,他本来已经做好要被骂一顿的准备,却没想到就这样被我轻轻放过,客气的语气好像还是我自己做错了一样,从此留了印象。
后来同住一舍,觉得缘分至此。那夜我乘夜色而去,他并没有睡着,就看着我走进月下,木槿花旁。从此他心里就落了个解不开的难题,辗转几夜,才晓得这题非得要我来解开答案。
一撞倾心,我何尝又不是如此。
此前我也未尝不是没听过同性恋人,书上就有龙阳之好的典故。我只尊重,但仍觉得一男一男,怎么言爱而组建家庭。
可我大概也是醉于霞光,听到这样的胡话第一时间想的居然不是拒绝,也不知如何应答。
好在泽成胆子大,见我没拒绝开心的笑着说:“阿来,你既是不拒绝我,我就当你答应了。”
阿来,阿来。他后面说什么我都听不见,只记得一声声的阿来。
之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依旧像以往一样一齐吃饭,去教学楼就分开上课。他下楼打球,我就寻个位置看看书听听歌,好不自在。只有他喊阿来喊的越来越顺口也越来越软。
我的失眠症也好上不少,为什么呢?
因为泽成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硬要粘过来和我躺在一起。我爱躺在床上拿着书看,他也要跟着我一起看。
“这段写得不好,怎么惠王既然是已经爱上了仵作女,又怎会让她亲身犯险。人都没了,何必到头来还要假惺惺地装给别人看。”
我原意不过是看一本杂书打发时间,没想到泽成却看得比我还入迷。
“那你呢?”我突然问起泽成。
“换作我,那也只能是我挡在你前面。”泽成敛了笑,突然认真地看着我。我不习惯,想收了书,不敢看他的眼睛。
夜里关灯,泽成也不愿意下去,就要和我睡在一张床上。刚开始我甚是嫌弃,夏天本就热,泽成就算冬日也像个大火炉(第一次的印象我仍记到现在)。然而鼾声四起时,泽成指腹轻轻摩挲着我的耳边,霎时间除了那夜的叶笛声和泽成规律的呼吸声,别的什么也听不见了。
湖边晚风吹过,这一晚一晚,竟也觉得凉爽。
秋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忙着期中。泽成要推演着各种我看不懂的数学公式,我也要写这令他头疼的长篇大论。泽成性格好,人缘广。可就连他也不愿回宿舍去陪着那一群呜呜渣渣的舍友,上回他的电脑终于不堪重负罢工,舍里的胖子还要催促着泽成去修。我看着也不舒服,虽然不爱说话,但文人的嘴皮子哪有不利索的,尤其是这群理院里混吃等死的腐木。真真是骂的那胖子面红耳赤,话都说不出来。
大概话音绕梁,从此整个院都知道了他不打扫卫生和各种奇葩事。
现在想想我大概活像个护犊子的老母鸡,犊子本人倒是乐呵呵地站在一旁观战。
只那胖子终于忍不住要上手,上演一出秀才遇到兵的戏码的时候,泽成把我拉过去,手一挥,脚一踹,直接把那胖子踹的一个没站稳摔到在木床上。
木床大概也受不了胖子长久的摧残,跟着泽成的电脑一齐宣告不伺候,还掀起一阵烟尘。
原来只是虚胖,看着唬人。
从此之后,我与泽成更是不愿意多呆,只是帮他们打扫完卫生,就泡在球场书馆或者教室,两个人哪都是自在。
数院的教授许是看着这一学期的研究生们心思都飘飞远走,发了狠,出的题格外的难,光是第一天得近世代数考下来,泽成的脸色就已经十分不好看。
我也不知如何帮助,毕竟数学的大门从未对我敞开过,我只能在一旁看书写字,陪着他温习到深夜。
不过结果倒还好,毕竟泽成聪慧,自己也努力,成了数院里侥幸没挂科的几个人之一。而舍友们自不必多说,他们都毫无准备还以为能像本科一样随随便便都能及格,结果当然全军覆没,甚至胖子还被老教授亲赏了个大大的鸭蛋,连些许对了的步骤和同情分都没有。
活像他,圆滚滚,只不过鸭蛋肯定要可爱的多。
泽成逃过一劫,我却要受刑。李先生就是我们院出题目的总负责人,他出题从不按套路,随心所欲却能最大程度考察学生们的功底。
我也就堪堪及格,拿着卷子给李先生一字一句的推敲琢磨,然后听取教训。
被骂的一度觉得我何德何能考上这所学校。
不过当我发现大家其实都差不多而且大都考的还没我高,我也瞬间不算太郁闷了。
而最后一点郁气被等在门外的泽成用一块大发糕给全送进了肚子里消化掉。
这家发糕离得更远,也不知道他要跑多久,总是是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