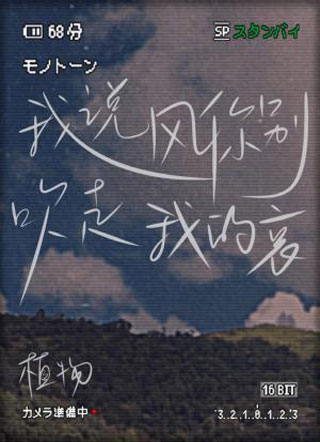
时间:2021-08-22 来源:长佩 分类:现代 作者:植物 主角:沈集岩 祝闻哀
不合适
“我看见她的时候,以为她只是喝醉了。她倒在排水管旁,头靠在大门后的水泥墙上,有人进出时,推拉大门的力度重上一点,她垂下来的脑袋就要被反复地撞。前一天夜里我出门时,一个陌生男人扶着不省人事的她,男人在打电话。我猜她钥匙一定又丢了,她身上散发酒臭,所以男人和我说谢谢的时候,我头也不抬,装作跟她没有任何关系。她醉得认不出我。我原来没打算在外过夜,但我无法面对她。我害怕她。第二天她衣不蔽体,趴在下水道上方,来往的人看见都要取笑她。我意识到她死了,即使这不是第一反应,但我很快感觉到了。我很平静。面对尸体我不知道怎么办。许熊过来带走了她,他送她去殡仪馆,等她火化,把骨灰随便找一处埋了,我猜是这样。因为许熊让我别跟着,他说了很绝望的话,对我说,于是我只能掩饰我远超于他的绝望。他说如果不是私自土葬违法,他根本不会管。那样我束手无策。我还想过把她背在身上,路人问我一句,我就说,喝酒喝死的,我找地方埋了。”
2021年8月1日凌晨三点,祝闻哀在江桥家楼下扰民,没把江桥扰醒,倒吵醒了他奶奶。江桥奶奶瞪了他一眼,阴阳怪气地骂了几句,才有些生气地帮他叫江桥。
听到祝闻哀说带他去买冰棍吃,江桥也骂他有病。
“大半夜你上哪去找!疯了吧祝闻哀。”
结果还真给找着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
夏里的温度数夜间最平易近人,但冰还是化得迅速。他们走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望去,祝闻哀眼里只有灯的颜色,没有其他了。路灯在守夜。
江桥这时问许梅怎么回事。
祝闻哀看上去毫不避讳,也没有停顿与犹豫。
说完以后,中间有一段刻意的安静,在黑夜的步伐里很突兀,但纺织娘的作祟与偶尔流过的稀罕的通勤车,让它不那么明显了。
江桥打破这样的尴尬:“闻哀,沈集岩呢?”
祝闻哀不解。
“你和他说了没?”
“有什么好说的。”
“你不告诉沈集岩……这事儿?”
祝闻哀垂眸,沉下的睫尾让江桥觉得有什么压在上面。他看起来想要说什么,但只是再次重复了一遍前面的话,“好像没什么要说的。”
“闻哀……你别蒙我。你跟沈集岩,是不是有什么——”
“不可能。”祝闻哀不留余地,“江桥,你觉得合适么?我跟他。”
江桥盯着他,然后停下脚步,将吃剩的棍棒扔向手边的垃圾桶。他一停,祝闻哀也止步,与他对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真的问我,还是已经有了答案,警告自己这很荒诞。
过界
室内昏暗,布帘紧闭着,不透光。窗外的昼与夜是薛定谔的猫。
祝闻哀睁眼,伸长手够床头柜上的手机,沈集岩的手机,告诉他现在是早晨八点半。
他口腔干,想喝水。祝闻哀掀开一角薄被,拎起脚边的裤子,同时打了个喷嚏。往床上看一眼,没动静。
他喝完水,接了半杯回来轻放在床头,又套了T恤。穿好以后站着愣半天,不知觉腰部覆上的手,沈集岩的下巴抵他的肩,声音有点低,有点哑,“在想什么。”
“回家洗澡。”祝闻哀答,前两个字咬得重,好像。
“不能在这洗?”
祝闻哀感觉腰上的力道有些加重了,也是好像。
他摇了摇头,“在哪都能做,但澡要回去洗。”
沈集岩低低地笑了,“在哪都能做?”
祝闻哀想说他会错意了,并自知接下去他将出口的话语怎样低俗。
“在哪,跟谁。都无所谓。”
果然,身后的人动作僵硬,连拂过耳侧的呼吸都受到感染。祝闻哀以为他会立刻松开自己,但他没有。他只是问:“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祝闻哀笑着反问,什么事啊。
“闻哀。”
“跟我讲。”
祝闻哀皱眉:“你怎么了?我们不是相互解闷的么,你管这么多?”
沈集岩松开了手。
他嗯了一声,解释方才的关心与逾越的亲密:“你误会了。生人闻泪都得递张纸。肢体动作也只是,习惯了吧。”
换而言之,和你做了,搂顺手了而已。
“嗯,我想也是。”
第二封咨询
夏天太沉了,松快的只有风。
2021年8月1日,祝闻哀发出第二封咨询:风,你能带我走吗?
清晨八时五十九分,我将许梅的钥匙插进锁孔,她丢钥匙丢惯了,某次拿走我的索性配上五只,四只放在我这,她说我保管东西比她靠谱。
一分钟之后,我面对卡死在锁孔中的一根金属,叫来了开锁师傅。师傅解释未必是钥匙劣质的原因,也可能门锁老化了。年久失修的旧楼诸多毛病并不稀奇。
后来师傅取出钥匙时,没下确凿的定论,我也没多问,任由门锁支撑到再报废的那一日。
折腾二十分钟,九点二十整,我回到家,换鞋之后习惯想去摸那棵残缺的植物,反应过来昨日将它扔了。
我每次都折它的枝,一根又一根,将它苟虐得光秃又丑陋,反正它活不了。在这里活不了,我救它,恩赐它阳光最充足、土壤最肥沃的地方,它不争气,一折就断。
难怪,许梅留下的东西,没一样好。
钥匙,植物,我。
我没有第一时间清洗身体。其实完事以后沈集岩就给我擦过了,我只是找个理由,做惯性逃犯。
家里没有人。许梅的房间连着厨房,我做饭,吃饭,烧水,喝水,用厨房唯一的窗看楼下时,都必须经过它,没有所谓的眼不见心不烦。
我的房间极小。一张床,一张书桌,基本没有空余。我要四仰八叉在地板上,借的是许梅的房间,反正房间就和厨房隔着一道玻璃门,没什么怪异。
我总不开灯,总盯着天花板那块漏水的角,这不是雨水,是楼上房客渗下来的。没人修,许梅在底下放了个盆便不再理睬,与对待我的方式如出一辙,除非积累的脏水飘出味道,她再叫我倒掉。
夏天太闷热。我没开空调,空调打上一小会儿也滴水,我嫌麻烦。
我感觉到我淌了许多汗,与木板紧贴的肌肤一层黏腻,却没有翻身。我发了许久的呆,不理屋外的敲门声与来电铃,许梅赊账的那位烟酒店老板娘在楼下催债,还效仿江桥砸玻璃,我一声不吭。躺到夜里十点十分,终于睡了几回,做了些梦,有好有坏,中间掉了几次眼泪,我累得不行,也没数到底几次。我的梦里,不是许梅就是沈集岩,我梦到许梅就一定会哭。
我醒来的时候满头大汗,睁开眼和闭着没有什么区别,都掉进了一片荒凉的漆黑里。这个季节在我这不茂盛,他人赞颂的绿色我说是草根燃尽的灰。夏又是芜秽的。
怎样复活死去的人?
我不如想,
怎样复活许梅。
许梅活不了,许梅已经死了。她趴在臭水沟旁边,她的淫乱放纵、低贱与不自爱,回以她一片肮脏污秽,给她带来周遭的嘲讽与贬低,带来我为她感到的自卑与难过、困惑与厌恶。
我从心底骂她。但是我顿时发觉了——意识到时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欲妄。这个叫祝闻哀的人蕴蓄了极度的龌龊与虚伪。我缠上沈集岩,三个月前与他约定做发泄工具,冠冕堂皇地满足私欲,又有多不堪。我意识到这个事实,我淫乱,放纵,低贱。我是第二个许梅。
许梅走了以后,我再也无法生活了。我甚至不知道她的骨灰埋在哪里。许梅去过绍兴,她告诉我那里有多美,要是能有机会去一次青岛就好了,她不知道她更爱哪个。
我每次远望山群的时候就想,那我去绍兴就好,青岛那么远,去不了就算了。许梅一定想待在绍兴,那样我就把她的骨灰带到绍兴,到时候见面再跟她说一声对不起:我原来打算青岛也去的,看看哪儿更诱人,就把你埋在哪,只是后来发觉就连绍兴都去不了。这个小县出不去了,群山包裹得太严密,里面的人苟延残喘,还想逃出去么?
山困住我了。
我想想算了,反正我这么讨厌许梅,许梅丢下我一个人,我在乎的不是“许梅丢下”,而是“我一个人”。想她复活是一时兴起。梦到一个人流泪并不一定是想念。
你能带我走吗?
我有意想扔掉生命时,同时猜想了如果呈现的问题是“我该怎么死”的情形。我猜测,回信十人,一半安慰我人生苦短,生命一程难得;另一半率先冷嘲热讽一番,然后叫我赶紧行动。
我不知道,或许我猜错了。当时我想到的只有这两种可能,而我毫无兴趣知道正确答案,我从来不要知道答案,我在逼我心里那个回答。
现在它有了:
许梅太孤独了。
哦,不。
是我孤独。
两日后,8月4日,祝闻哀在公交上,手心的温度发烫,远望,山不动。天好阴郁,雨水如期而至地下了,冲散微渺的一丝热,在高温的遏抑下燃成一道青烟,再融进从天而降的雨。
雾遮住峰峦,这样一片茫,他从山顶一跃而下,成了雨中、低云吞吐的景,与山间的松林融洽,葬礼一同交给大山底下的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