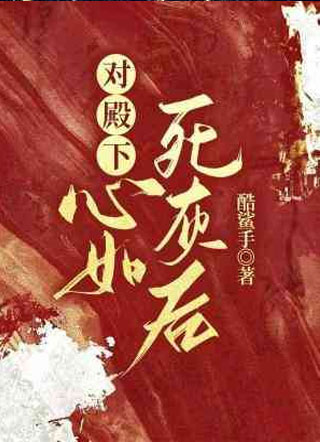
时间:2023-07-30 来源:长佩 分类:古代 作者:酷鲨手 主角:贺凛 贺凛
我避开了暗哨,蛰伏在季府尖翘重檐之上。
只见一顶金银绣透雕肩舆从季府缓缓抬了出来,肩舆右边的窗牖半敞着,里面的帘子被疾风吹了起来,露出了一张年轻的面容,瞬息之间,那帘子复垂了下来,就连窗牖也被重新掩上了。
只需一眼,我就认出来了。
倚在肩舆里的青年正是内阁首辅季沧海与他那老妻所生的长子季听寒,正是我这次的任务对象。
肩舆一路从神武大街抬到了高头街狭窄的巷道里,到了寻芳阁才堪堪停下。
轿夫落舆,小厮打了帘,扶着季听寒从肩舆里走出来。
季听寒是寻芳阁的熟客,他才刚下肩舆,寻芳阁在外迎客的姑娘们看着他来了,都提着裙裾如同潮水般涌了上来,那些个姑娘都生得丰盈貌美,身上擦着浓郁的脂粉,一个劲儿往季听寒身上凑,季听寒也是个不规矩的,还没进屋,就揉捏着姑娘丰润的臀,把姑娘弄得燥红了脸。
看到这里,我忍不住想干呕起来。
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这种事情,简直是有伤风化、不堪入目!
但为了能够完成贺凛交代的任务,我只能强忍着身体的不适,继续监视着季听寒。
只见姑娘们笑靥如花地缠着季听寒的小臂,迎着季听寒进到寻芳阁,季听寒没有在大厅多做停留,而是去了雅间。
我攀到了屋檐之上,身体蜷伏着,指尖拨开屋檐上铺满青苔的瓦片,从屋檐上观察着季听寒的一举一动。
原本我以为季听寒是来找姑娘寻欢作乐,却没想到,季听寒进了雅间,就将原本揽在臂弯里的姑娘逐了出去,单独坐在案几旁的蒲团上。他动作熟稔地将阳羡雪芽的茶饼置于烧得滚烫的炉子上,轻唤一声:“出来吧。”
我对季听寒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感到震惊。
这季听寒对外一直都装成了纨绔子弟的模样,可如今看来,季听寒并不是只知道花天酒地的就哭,更像是善于伪装、心思深沉的世家公子。
季听寒是季沧海的长子,要是他太过出色,难免会被嘉定帝所忌惮,若他装成了酒肉的纨绔,嘉定帝便不会疑心到他身上了。
想到这里,我顿时觉得季听寒也是个不好相与的人物。
片刻之间,一位身穿常服的男人从屏风后走了出来,坐在季听寒的对面,在看清男人的脸时,我惊愕不已。
来寻芳阁见季听寒的竟然是六部之一的刑部尚书江弄清,他在朝中处于中立,可谁知道他私底下竟然与季听寒有所往来。
我的眼底紧缩,将耳朵贴紧了屋檐,视线一瞬不瞬地盯着里间的一举一动,生怕错漏了什么重要的信息。
季听寒面前的茶饼被炙烤得熟透了,他用镊子夹起茶饼,稍凉后将其捣碎,放在茶碾中,头也不抬,“宋兆的案子审得怎么样了?”
“宋兆的案子是交给三司会审,我们刑部不好在里面插手。”江弄清觉得口干舌燥,胡乱地接过了季听寒为他斟的茶。
“夜长梦多的道理,江大人应该比我更懂。”季听寒的唇沾了茶,气氛却变得剑拔弩张,危险的气息一触即发。
江弄清没有再喝茶,低着头,也不退让:“刑部可以结案,但公子就不怕惹得自己浑身腥臭吗?”
季听寒的指腹搭在杯壁上,“江大人,稍安勿躁。三年前陛下拨出去修缮桑干河堤坝的二十万两白银,都被朝臣给分了,宋兆知道自己终究难逃一死,就将这份名单写了下来,现如今这份名单被他藏了起来。要是这份名单落到陛下手里,别说是你,就连我父亲都有可能会被陛下责问。”
江弄清脸上的脸色并不好看,他呼吸微滞,扶着茶盏的手竟然在发颤,眼底似乎撩烧起无法泯灭的烈火,又似乎有几分隐蔽的癫狂之色,“季公子这是在威胁我?”
“这不是威胁,而是忠告。”季听寒处变不惊地将红炉里的茶分进茶盏中,“你我如今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做与不做,全看江大人了。”
江弄清的手臂上突兀浮现起几道经络,呼吸也比之前来得沉重,咬牙切齿地瞪着季听寒,“三日之内,刑部会结案。”
说完以后,江弄清疾步走出了雅间。
望着江弄清的背影,我的心脏陡然狂震了下。
要是能提前拿到宋兆手中的名单,在京察时把名单交给嘉定帝,那么季党跟秦党都会栽个大跟头。
我必须快点将这个消息告诉贺凛。
想到这里,我动作极轻地将瓦片覆在屋檐上,转身离开了寻芳阁。
风雪交加,天寒地冻。东宫的朱墙外都积着一层雪,这凝结出尖锥似的冰挂,在日光下透着薄光,待日头大了些,这雪便要化成水。
我绕过了东宫外的朱墙,经过了垂花拱门,来到了东宫的寝殿。
寝殿里烧着地龙,空气里还漂浮着些许的药味,但有一股更为呛人的熏香将药味给掩住了,要不是我的嗅觉灵敏,也一定闻不出来。
我绕过屏风,看到了福宝正伺候着贺凛喝药,我的眉心微跳,目露忧光,“殿下。”
福宝将定窑珐琅彩折腰碗收到托盘上,替贺凛擦拭了唇角,又替贺凛将衾被掖好,这才躬身退下。
贺凛的脸色是像雪一样的惨白,他摆了摆手,指尖透着虚弱的白,“可是有眉目了?”
见贺凛问起了政务,我也不好再问贺凛的病情,只能先将疑惑都吞进腹中。
我走到贺凛的软塌旁,跪伏在贺凛的身侧,“属下跟着季听寒去了寻芳阁,他并不是去寻欢作乐,而是借着逛窑子的名头,去私见刑部尚书江弄清。”
“玩世不恭是季听寒的保命符,他若是太过精明能干,陛下恐怕也容不下他们季家。”贺凛屈起指节,揉着额穴。
我顺着贺凛的话往下说,“季沧海生了个好儿子。”
贺凛停顿半晌,转了话头,“他这时候去见江弄清,是为了宋兆吧?”
我脸上的表情微征。
方才我只是提到了江弄清,贺凛却仿佛能看透这个名字,窥视到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拢紧袖摆,斟酌着用词说:“是,他想让刑部结案,但江弄清上头还压着好几个他开罪不起的老顽固。起先江弄清并不同意结案,但季听寒却拿宋兆手头有一张私吞修缮桑干河银两的名单来威胁他,他不得已同意了。”
“赶在刑部结案前,拿到宋兆手里的名单。”贺凛倏然捂着唇,剧烈地咳嗽起来,他的胸腔都被咳得震颤起来。
我看着贺凛骤转急下的身体,心底紧张得不行。
我眼底通红,喑哑着声音说道:“属下去给您找太医。”
“不准去。”
贺凛的面色发白,神色阴郁,鬓边都涌现出了薄汗,他白的近乎透明的指尖攥着我的手腕,像是要将我缚在寝殿里。
我的身体遏制不住地发起抖,嘴唇发颤,声音像是蒙着哭腔,“为什么?”
骤雨狂风不断冲刷着廊檐,透过了纸糊的窗牖涌了进来,寝殿的烛火被吹熄了,软塌旁的帷幔如同海浪般汹涌起伏着,发出了刺耳的声响。
雷声接踵而来,劈在窗牖上,一道白光窜了进来,罩在贺凛的珠玉般的侧脸上,他的眼神平静,双唇是毫无血色的白,像是随时都有可能会丧失生命,声音骤然发冷,“谁都能起疫病,而孤不能。”
“什么疫病?”我不可置信地望着贺凛,心脏像是漏掉了一拍。
贺凛漆深的瞳孔倒映在白光里,指关节攥着我的腕骨,像是要将我生生撕烂,“都说旱涝之后,必定会有疫病。这几天桑干河的堤坝是修筑好了,可原先浸泡在桑干河脏水里的难民、禁军,浑身都起了热,有的还会咳嗽,经过太医的诊断,发现这是疫病。”
听到这里,我的心凉透了。
当初贺凛去桑干河,与工部的胥吏一起泡在桑干河里讨论修补堤坝的法子,回来以后,身体都泡白了。
要是难民们是得了疫病,那贺凛如今这症状也应当是患了疫病。
我的眼睛像是氤氲着灰蒙蒙的雾气,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贺凛不想被人知道他起了疫病的原因,我再清楚不过了。
他好不容易爬到了如今的位置,他要是起了疫病,那么“秦”、“季”两党定然会挑唆嘉定帝将他的权势撤走,从始至终,于他而言,那些权势只是他的保命符罢了。
想到这些,我的心底愈发难过起来,胸腔像是被水泥堵住,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在贺凛的深沉的注视中,我垂下了头,眼尾潮红,声音闷得惊人,“属下不会让别人知道您起了疫病。”
贺凛像是终于听到了满意的答案,他松开了手,疲软的身体往瓷枕上靠。
窗牖外的雨势渐渐小了,贺凛的身子却遽然热了起来,好似是滚烫的烧红烙铁,光是碰一下,便会觉得烫得要命。
我的年龄小,但也知道要怎么照顾人。
要是身上起热,可以拿冰块退热。
换了从前,东宫自然可以到御膳房里取冰块来退热,可此时要是去了御膳房,定然逃不过季贵妃的眼线,要是被季贵妃知道,那后果不堪设想。
我望着窗牖外的雪水,陷入沉思。
片刻后,我走出了寝殿。
我褪下了身上的外袍,赤裸着上半身,在寂静无声的院子里跪了下来。
雨停了,风雪像是尖刀一样剐在我的皮肤上,而我却浑然不觉。
只要能帮贺凛退热,我做什么都甘之如饴。
我在雪地里跪了一盏茶的功夫,唇色被冻得青白发僵,身躯冷得像是重檐上的冰雕。
我支着身子,从雪地里爬了起来,跨进了寝殿里。
软塌上的贺凛意识涣散,鬓边沾着湿汗,嘴里喊着一些破碎的言语,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我隐约能感觉到他是在做噩梦。
“别打了,疼……”贺凛的脸色如死灰,他的手指蜷着寝衣,血管骤然突起。
我脱掉黑靴,爬上了软塌,将浑身湿透的贺凛从软塌上捞了起来,手臂紧紧抱着他的身躯。
这是我第一次与贺凛如此贴近,隔着薄薄的意料,我听到了贺凛心脏跳动的声音。
为了安抚贺凛,我回想着阿娘幼时照顾我的样子,轻轻拍着贺凛的背脊,小声哄着:“没事了,没有人打你。”
贺凛没再出声,他的下颔垫在我的肩臂上,气息比之前均匀一些。
我撩开了贺凛额头上的湿发,试探性地抚着贺凛的额头,发现贺凛身上的温度确实低了不少,但还是比我身上的温度还要高一些。
我将贺凛重新放倒在软塌上,然后折返回小院里,等我身上变冷以后,再重新去寝殿里为贺凛退热。
反复做了四五次以后,贺凛身上的烧大抵是退了,温度总算是与我差不多了。
悬立在峭壁上的心总算是落地了,我心中喜不自禁。
门口倏然传来了一阵急切的脚步声,我警惕地忘了过去,这时候能来东宫的人,必定得是贺凛的心腹。
我抬起下颔,视线与寝殿门口的郑庭川四目相接。
郑庭川一身黼衣,衣摆垂直于地,宽阔的绣摆被风雪吹拂而起,露出了他细瘦的腕骨所缠绕着的红绳。
我见过那条红绳,那是贺凛在跪了三天三夜在甘露寺求来的红绳,具有祈福消灾的作用。
我原先不知道贺凛为何要求那条红绳,如今却是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