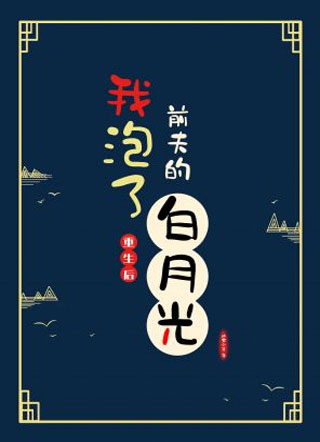
时间:2023-04-25 来源:寒武纪年 分类:现代 作者:快乐小鲨 主角:唐演 谢寅
华灯下的冰冷湖水接二连三地倒灌进口鼻,唐演胡乱挥舞挣扎着左手手臂,最后在一个猛地喘息之中坐起身来。
他大口大口躺在床榻上面喘着粗气,身上的劲儿愣是好半天都没有缓过神。
疼痛好像是从脑袋里面生长出来的瘤子,开始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反复作祟。
在眩晕与混乱之间,唐演再次支撑不住身体,直愣愣朝着后头又躺了下去。
后背没有了那股强行压制着他的力量,他才是难得轻松地喘息了一口气。
在接连呼吸了好几口新鲜空气缓过劲儿来以后,唐演才缓缓睁开眼想观察自己现在是身处何地。
早先他为了躲避那些搜查的追兵东躲西藏,接连几夜都是留宿在已经被废弃的破庙里。
原本他是打算等到唐家一事全部过去,再想办法换个新身份生活以及为唐家翻案。
但显然幕后黑手很了解斩草除根这个道理,整个京城封锁了接近半月,追捕的士兵却是不减反增。
彼时唐演已经三天没有吃过一口热饭菜,最终在晚上饿得实在是受不了准备蹲在河水边灌水充饥。
谁知出门不过一炷香时间,他就被人找到。
那些黑衣人摁住他的头顶,将他的脑袋狠狠摁在了深秋那冰冷刺骨的水里。
可笑的是,那明明还不到他膝盖的浅滩,竟然就成了他唐演的最终归处。
随着唐演睁开眼,窗外的一点和煦天光刺得唐演有些发愣。
他现在所在的狭小房间里,有光,有桌椅,甚至还有一张暂且可以睡觉的榻子。
破庙里面可没有这些。
唐演的第一反应是自己被人救下来了。
可这想法转瞬即逝,一种无比陌生的熟悉感却开始侵占他心底的每一个角落。
窗外并未下雨,几道光线从有破洞的窗户纸径直落在了他的手臂上,房间里一张床就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位置。
他身下的床榻很硬,上面只随意搭了一张春季的薄被,没有枕头,而他现在枕着的是几件脏兮兮的旧衣服。
明明是不知道多少年前的记忆,唐演却在这一瞬间回想起来了这地方是哪里。
安河镇知府府衙,查家。
他生活了接近十四年的地方。
唐演的娘亲曾经是副丞相唐家唐老爷的妾室,说是妾室,倒不如直接说是个爬床的。
在京中任谁都知道,副丞相唐老爷唐严致与其妻子胡璇樱是少年夫妻,两人关系极好,胡璇樱也在唐严致登上副相位置之前已为他孕育两子。
唐严致曾很明确说过此生后宅宅院唯有胡璇樱一名夫人,众人本以为不过玩笑。
可十余年过去,胡璇樱与唐严致年岁渐大,也确实未曾见过唐严致再抬人进后宅当中。
唐严致对情感的忠贞总是京城人士彼此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而这话题很快就被唐演的娘亲打开了一条裂缝。
唐演的娘亲是当年唐严致政敌送去的人,结果最后却爱上了唐严致。
她迫切地想要利用自己周身的一切来绑住唐严致,再加上背后势力的催促,她用计让唐严致留在了自己的房中一夜春宵。
这一夜,便就有了唐演。
看在竟然是个儿子的份上,唐家的老夫人让唐严致将他的母亲以妾室之礼迎进了家门,可唐严致并未因这个儿子而对自己母亲有半点好脸色。
最终自己母亲才诞下自己,便就因为郁郁寡欢而撒手人寰。
至于唐演,便就被唐严致送往了远离京都的安河镇。
到底是丞相府送出来的人,起初地方府衙还是不敢怠慢,好吃好喝供着。
后面见丞相府这么多年的不管不问,这地方知府的人个个都是人精,哪里还愿意讨好一个小公子哥?
于是唐演在九岁的时候就被查家以“厢房不够”为理由,将他赶到了小柴房偏侧下人都不愿意居住的地方。
原本他们就想那样将他饿死,或者说是将他逼迫到忍无可忍自行离开,可唐演小时候就是一根筋。
他们说厢房不够,唐演就自行搬离,生生熬过冬冷夏热。
他们说缴纳不起书院学费,便就叫唐演留家自学,丢了一堆残破的书籍让他自学。
在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先传出来他唐演的身世,自那以后,就是府中的下人也大多看不起他这位京都来的庶子。
从那以后,唐演便就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哪怕是重病也多亏他福大命大,硬生生扛了过来。
并且在安河镇时,查家的小儿子也敢时时刻刻欺压在他头顶上。
他甚至在安河镇里,残废了一只手。
一直到十五岁被接回京都以后,唐演才意识到他在安河镇的生活究竟有多么可悲和糊涂。
长久在压抑环境里面生活,唐演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处于极度自卑的状态。
他不敢与京都的公子们走在一起,也不敢出门,唯恐出去就被人嘲笑他没规矩,没气度,蠢笨无知,以及——是个残废。
唐演花了很多年时间,才将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
由于庶子身份,唐严致并不允许他如他的两位哥哥一样入仕,但也因愧疚,在暗地里给他提供了很多金钱上的帮助,让他去学习经商。
为了做好这一件事,唐演在人生的后数十年里,游遍天下大川,逛尽五湖四海,即便身有残疾却胸怀天下,他见到饥荒时候饿殍遍地,也在走商时经历过几回战役,年少的不甘使得他怜悯世间受尽磋磨之人。
他广修善堂、捐赠灾区、在民间留下了一个大善人的称号。
原本唐演想将自己所作出的功绩呈给唐严致看,却在刚进家门的时候得到消息。
唐家人因为私藏火药军库,暗地培养势力意图谋反,判满门抄斩,唐严致与他的两名哥哥在唐演回来之前已被收押,缉拿唐家其他人的官兵则已快到家门口。
唐夫人胡璇樱为了不连累唐演,在众人面前与他堂前三击掌,断绝所有关系。
唐演这才从要掉脑袋的事情里面被摘除出来。
彼时所有人都在说这唐家到底有多么不喜唐演这个庶子,就是死也不愿意同他一并上黄泉。
唯有唐演自己知道,唐夫人是为了救他的命,让他在逃出去以后想办法为唐家翻案。
唐演很清楚唐家绝非通敌卖国谋逆之人,在逃出去后第一件事,唐演就想要先联系自己在京中的势力帮忙。
可他悲哀地发现,他这么多年来四处走动,哪怕势力也大多不过是商贾之家。
和朝政半点边都搭不上。
都说金银维系起来的感情最牢固也最脆弱,在唐家倒台过后,唐演一夜之间成了孤家寡人。
没有办法,唐演只能退而其次,想要先出了京都,再看看能有几人能愿意帮自己。
然而这想法还没实行,天家就先下令封了城。
说是追查唐家暗信联系的余党,可唐演却知道,这是明晃晃冲着他来的。
记忆停留在窒息的最后一刻,再睁眼后,他唐演便就又一次到了这儿。
回到了还在查家的时候!
唐演上辈子行商走过很多地方,对鬼神之说倒也存有几分敬畏之心,可却也从未前世今生这种好事竟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喂!小杂种!你竟然还敢睡!?你快给我滚出来!”
尖利的嗓子伴随着砰砰的敲门声打断了唐演的思绪。
唐演还顿了下,才迅速将这个声音的主人从自己杂乱的记忆里面揪了出来。
查家的小公子查昌。
在前世的时候,这位小公子可谓是唐演小时候一道挥之不去的噩梦。
自从他从他自己父亲那里知道自己没有后台后,便就率先揭下了面具。
到底是小孩,不必谁教导恶事就能干上一大堆。
比如说故意在冬天的时候将他的被褥浇湿,刻意拖着自己不让自己发现,而等到他发现想要更换的时候已然夜深人静,无人搭理唐演。
唐演也就只能抱着在寒冬里抱着湿漉漉的被单睡觉。
又或者说是在京都来人问话的时候,故意将他推倒进池水里,害得他高烧,便就有苦也不能和京都的家里人告状。
令唐演最为印象深刻的其中一件事,便就是有回查昌冲进他的房间,把还在重病高烧的他从榻上赶起来,要他去后院挑水缸。
挑水缸本是最下等粗实婆子才会做的事情,夏天还好。
冬天水面结冰,要想挑水就得先将水面的冰凿开,而后灌满水,再挑走。
这样反复几回,人的手就会生生冻僵冻红,不必过夜,傍晚就能长出冻疮。
而查昌为了折磨他,冬天一旦是心情不爽,就会让唐演做这件事。
唐演可以感觉到那个时候的查昌心情极差,他知道自己在查家没有话语权,也不敢反抗,只能反复做着这样的事情。
往常查昌吩咐完以后就不乐意站在寒风里等着他,可偏偏那次不同。
在唐演战战兢兢的时候,查昌却是猛地一抬脚踹在了唐演的后腰上。
彼时的唐演本就重病未愈,一个不稳,直接朝着地面栽倒。
水缸在地面上砸到粉碎,而在唐演的不远处恰好有一块尖利的石块,他的右手掌心便就这么直愣愣地被石头的尖端穿透。
在钻心刺骨的疼痛里,唐演听见查昌快意的哈哈大笑声。
后来唐演才知道,那回查昌挨了夫子的板子,又听见夫子夸赞自己哪怕不去书院也成绩很好,心生嫉妒,故意要毁了他写字的右手。
在痛晕过去的迷迷糊糊中,唐演还听见查昌在自己耳边骂:“小杂种就是小杂种,看你没了手,还能怎么写字。”
而也正是这一道伤口,造就了唐演后面数十年时间的残废。
吓人的伤疤落在掌心十余年时间,直至最后唐演想挣扎开黑衣人时,这只右手也使不上力气。
想到这里,唐演忙抬起自己的右手看了眼,随后便松了口气。
还好,手还没有受伤。
约莫是长久没有听见房间里面,查昌一脚踹开了房门,骂骂咧咧从外面闯进来。
“喂!小杂种!叫你呢!你他妈没听见是不是!?谁准许你今日偷懒了,我老子让我抄书献给什么巡抚,明日他们就要来人,你赶紧给我起来帮我,再不起来,小心我抽你!”
抄书?巡抚?
唐演忽视查昌难听的叫骂声音,优先将注意力放在了对自己分析情况有利的字眼上。
不消一会儿,唐演就回想起来了这回事。
不得不感叹他这重生回来的时间可真是刚刚好。
如果他记忆没有出错的话,现在应当是他十四岁那年的秋,而他的手便就是在今年年末的冬季被查昌毁掉的。
其实在上辈子,唐演也回想过很多遍,查昌往日里面因为成绩不如他也被夫子拿来比较过多次,为什么偏偏就那一回敢铆足了劲儿要毁掉他。
后来有一回唐演故地重游,再来这早已空无一人的查府时,遇见了当时已经被革职查办又被放出来的巡抚大人。
那位前巡抚看见他很惊讶,但也对他残废的手表示了十分的惋惜。
唐演亲耳听见那位前巡抚对他说:“当时那查家小儿在秋末时赠了我一本《兰亭序》字帖,说是佩服我的能力,想叫我多多教导。可我一眼就看出那字帖并非是出自那查家小儿的手笔,后头想到您当时住在查家,便就知道是出自于您手了。”
“后面我将他的字帖退了回去,叫他要自己好好学习。哎——我还记得您当年不过十四,就能将王羲之的行书练得出神入化,若是手没有出意外,您恐怕现在早已成书法大家了。”
这样迟来十多年入耳的夸赞大概是在查昌献上字帖后就入了查昌的耳朵。
以至于联系起前十多年的愤怒,最终在那个冬日里引爆。
前世时候十四岁的自己从未想过自己竟然还能反抗这回事,也没有深究过查昌为什么说明天巡抚要来,今天却让他起来抄字帖的事情。
现在想来,恐怕是巡抚已经到了半日。
查昌这个蠢货眼见自己那个知府老子对巡抚点头哈腰,也想跟着巴结一二,这才急匆匆来找他,要他写出字帖拿去送人。
前世种种当时看不明白的心思,却是昭然若揭了。
唐演这边还在回想前世今生的种种细节,这边的查昌便就已经按捺不住。
他见唐演竟然现在都敢不搭理他,两眉一竖,挪着肥胖的身体就要冲过来抓唐演,嘴里的骂声更重。
“小杂种,我和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吗!?”
他嗓音不像是成年男人那样醇厚,又不如孩童般清脆,正是变声时期最为沙哑难听的时候。
再配上那些难听的话,活脱脱将自己表现得像是个市井屠夫,肚子里面没半点墨水似的。
唐演半眯起眼看向朝着自己冲过来的查昌,右手手臂也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又一下的抽痛了起来。
当年从他摔伤到被发现,再到请大夫,足足已经过了半日的时间。
为他医治的大夫说他本身就伤势过重,再加上延误了医治的最好时机,往后这只手就只能是端饭端碗了。
那时唐演还不明白只能端饭端碗的意思,还自我安慰,还好,手能保住,不至于当真什么都做不了。
可当他痊愈以后,他却发现,自己再也端不起来任何重物。
哪怕端饭端碗也需看状态如何,状态好的时候倒能举起来一两分钟。
状态不好的时候,莫说是端饭端碗,就是拿筷子他的右手都会抖个不停。
这还不算,每每阴雨冷天,唐演的右手还会有冻疮反复发作,那疤痕下的伤口则像是又得了雨露的恩情,开始不顾他意愿在他的皮肤下面生长。
钻心的疼痛和痒让人感到抓心挠肺,无论是用什么药都没有用处。
在前世好几回,唐演都曾用小刀在自己右手疤痕上比划,思索到底要不要将这伤口划开放血止疼止痒。
前世的时候,也更是因为他的这只右手而受了不知道多少人的冷眼,直至他学会用左手生活写字,那些嘲讽的声音才略微下去了一些。
疼啊。
当真是钻心刺骨的疼。
唐演回忆起来曾经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事情,先是悠悠地叹了一口气,再摊开掌心在脏兮兮的被单上反复摩挲了两回来缓解小臂的抽筋。
这动作是当真把查昌惹怒了。
查昌三步并作两步,抡起胖到连关节在哪里都看不见的手臂,朝唐演的脑袋上就要打过来:“小杂种——!”
“你敢打下来试试。”
唐演的声音低哑而平淡,一句话说得不急不慢。
没有过去一样那种畏惧,倒是让查昌愣了一下。
查昌这才注意到唐演现在苍白的脸上平静到可怕。
原本唐演的长相就偏向阴柔一些,再加上这么多年在查家被磋磨着,每回查昌见他脸上都是畏惧和满是愁绪的样子,没有半点反抗的勇气。
这还是查昌第一次在唐演的脸上看见这种表情,谈不上是威胁。
可偏偏就是有一种叫人两股打颤的气质从他骨子里面散发出来,就连他眼下那两颗艳红色的红痣都仿佛是成了衬托他金贵与上位者的面相。
查昌要打下去的手顿在半空,紧接而来的便就是被反驳时的怒火。
——他唐演算个什么东西!?现在竟然敢命令他了!
“我就打你了!”查昌骂道:“你以为自己是谁啊?不过是个爹娘都不要的小杂种,我听我爹说了,你娘是个爬床的贱人,你就是小贱人生下来的小杂种!”
说罢,查昌的胖手带着风就朝唐演的脸再次打了下来。
现在的唐演可不会惯着查昌一星半点,眼见着那只手就要落在自己脸上的时候,唐演直接往旁边一躲,查昌的掌心就硬生生劈在了木制的床榻上。
这一下疼得查昌龇牙咧嘴,哎哟哎哟的叫唤。
这还没完,唐演趁他还在叫疼,一把将床头的旧衣服堆掀到了查昌的脑袋上。
不等查昌将衣服扒下来,唐演就直接隔着衣服布料朝查昌的脑袋上来了一拳头。
用左手打的。
查昌本身就吃得上宽下细,根基不稳。
这一拳头下去把他打得眼冒金星,硬生生是一屁股坐在了门框上,好半晌都没有回过劲儿来。
他约莫怎么也想不通这往日里见到他就和老鼠见到猫一样的唐演怎么敢跳起来打他。
可唐演没有打算就此放过他。
都说小孩子做坏事都不过是因不懂事,而偏偏查昌的不懂事几乎是害了唐演半生之久。
前世因为右手残废带来的嘲笑开始在唐演的脑海里再度响起。
除却那些难听的辱骂,还有自己刚开始学习经商要学写账本、打算盘这些事情都被教习师父说“要是你右手好好的,速度就能快上许多了”。
还有前生那个人捧着他的双手望着他的脸叹息:“要是你的双手没有废掉的话,应当还能为我做更多事情才是。”
亦或者友人的关心:“你这只手,当真治不好吗?”
治不好!
永生!
永世都治不好!
如若并非是重来一遭,他唐演,哪怕是到死,也要拖着这么一只残废的手下到阴曹地府里去!
极致的愤怒冲上唐演的脑袋,竟是冲淡了这具虚弱身体里因病痛带来的不爽利。
唐演骑在查昌肥胖的身躯上,用尚且完好的右手狠狠摁住查昌的肩膀将他固在地面。
隔着几层带着汗味的脏衣服,狠狠用做手朝着查昌的脑袋与身体砸了下去。
查昌原先还想反抗,嘴里面更是骂骂咧咧着一些难听的话。
在又一拳后,查昌脸上盖着的脏衣服被唐演的拳头带了下来,他看见了唐演脸上的表情。
那简直就是阴曹地府爬回来的恶鬼,好像就是不把他带下去就不罢休似的。
查昌是真的怕了,刚才的嚣张气焰也在瞬间被浇得星点不剩。
他想站起来逃掉,可唐演整个人都压在了查昌的身上,分明看着瘦瘦小小一个全是骨头,却像是一座泰山,压得他动不了身。
“哎哟!别打了!别打我了!我错了!”查昌扯着嗓子大哭大叫干嚎一样叫嚷。
可这周边没有一个人过来。
因为查昌以往打唐演,唐演也是这么和杀猪一样嚎的。
后面在他被他的知府老子骂了几次以后,查昌往后要找唐演什么事情,都是先将人支开再来。
这也正是为什么当时唐演手撞在石头上后没有被第一时间发现的原因。
眼见求饶没有用处,查昌便就也不继续求了。
他一边用手拦住他自己的脸,一边叫叫嚷嚷骂:“呜呜呜我要告诉我爹,小杂种!小杂种!你这个该死的小杂种!我要告诉我爹把你赶到街上去讨饭!!”
让他老子把自己赶到街上要饭?
他老子敢吗!
前世唐演回了京都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原来京都唐家每年都会给安河镇查家一大笔的抚养费。
唐夫人家族是经商的,尽管后面没落,可手中的财富一天散一百两出去也能散到她下辈子。
而在上辈子的时候,唐演没有见过那些银子毫厘。
尽数都被查知府还有从唐家来的人合并吞了个干净,使得前世唐演在安河镇的十四年都悲惨无比。
唐演听他这止不住的叫唤已经累了,他气喘吁吁地将视线在房间里面转了圈。
再从查昌的身上站起身来走向了窗台——那里放了一把已经生了锈迹的剪刀。
查昌瞳孔紧缩,欲哭无泪,也顾不上被打得快要散架的身体,连滚带爬就要从屋子里面逃出去。
唐演哪里是被逼急了?
他这是要杀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