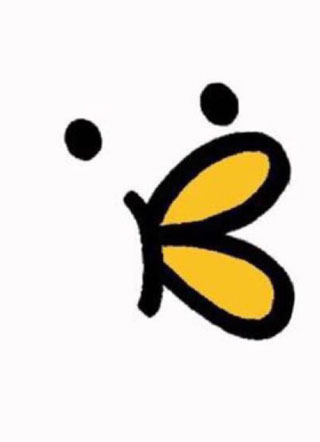
时间:2023-03-19 来源:长佩 分类:现代 作者:啃大葡萄 主角:金离 陈景辉
“他还在发烧吗?”
“是的,小陈总。”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佣人退出去了,偌大的房间只有陈景明手机屏幕上一点光亮,金离躺在黑暗中,宽大的羽绒被使他看起来像一条案板上的鱼。
金离本来就睡得浅,被细微的对话声搅醒了,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声:“哥?”
这下陈景明不再能悄无声息地退出去。
从门口到床边的距离,硬是被他捱了半天才走完。
“小离,还没睡吗?”
“嗯。”金离坐起身,打开了床头柜上的台灯,亮起一小片暖融融的光,陈景明甚至可以看清人脸上细小的绒毛。还有洗漱后顺下的刘海,显得人格外稚气。
窗外应声响起一声惊雷,是江城罕见的“雷打冬”。
本已坐起来的人倏地又缩进了被子。
“早点休息吧。”
陈景明说完转身就要走,被人拉住了灰色卫衣的下摆。
他今天本来穿的是西装,为了去学校参加延毕的答辩会准备的。
说是答辩,其实更像单方面训话。在听完了他昨晚临时准备的PPT后,几位老师轮番对他最后一学期最后两个月的摆烂表示不解。
“这要是本科论文就给你过了,但你这作为研究生,这个质量,这个模型一点自己的数据都没有,全是文献引用,我们想帮你也没办法啊….”
“还有最后一门课你不来考试,你这学期就这一门课了,学分占比很高,这怎么办…”
陈景明点头点累了,索性端坐着沉默。
接着无非又是一些浪子回头,十年不晚的车轱辘话。
经历了这番精神损耗,出校门时他松了一大口气,抬表一看,时间还早。
不想回家,一时也想不出哪里好去,开着车四处乱逛,不知怎地就开到了乐天湖。
在城市化日益普及的今天,既不想离市区太远,又想享受一下自然风光,人们多半会选择这里。
他到的时候是下午一点多,阳光正好,冬日的光线绵绵的,隔着云层洒到身上时似乎只有薄薄的一层。
有几对家长带着孩子出来露营,花花绿绿的餐布,用饮料瓶压住四个角,餐食也挺丰富。大人还在搭帐篷,一个小孩手里拿着一根卡通图案的棒棒糖,举得高高的,在前边跑,另一个跟在后面追。
不一会前边的那个栽了个跟头,手里的糖摔出去老远,快要碰到陈景明脚跟前。
摔了跤的小孩头发上都粘着草,眼泪啪嗒啪嗒掉。后边的那个看到了也顾不上糖,蹲下来帮他清理头发,又问他“痛不痛?”
地上的小孩点头。
蹲下来的小孩就摸了摸对方的头,摇头晃脑地来了句“痛痛飞。”
陈景明被逗乐了,弯下腰把糖捡了起来,几步走过去还给小孩。
这时家长也过来了,向他道谢,拉起两个小孩走了。
他突然想起七岁那年,陈舱带着他们哥俩和金离一块来湖边玩。
那时距离那场夺走他的母亲贺一吟和金离父母生命的火灾才过去两个多月。
一路上气氛格外沉重,陈舱在驾驶座试图活跃气氛,问他们谁想吃棉花糖?
一开始没人搭话。
沉默又蔓延了几个红绿灯,陈舱打开车窗。
陈景明现在还记得那时涌入鼻腔的气味,尾气里混杂着新鲜空气,像参着胡椒粉的棉花糖,让人有点想吐。
气味随着陈舱点燃香烟的动作变得更糟。
金离先开始呕吐,吐在那个装水果的塑料袋里。呕吐物淹没了盒装的反季西瓜和应季草莓。
陈景明接着也吐了,但已经没有第二个袋子,所以他从金离手里扯过一侧拉环,他们头碰头地吐了个痛快。
陈舱不得不把车停靠在路边,那根烟还没抽完。陈景明和金离在草丛边用矿泉水漱口,又用同一瓶水洗手。
陈景辉在用湿巾纸擦拭后座,又喷了好几下车载清新剂。
后来的车程陈舱没再和他们搭话。
在乐天湖往南大概三公里远,有个陵园,取名达观。他们过世的三位至亲就葬在那里。
陈景明回过神来时,天都黑了,还下起了小雨,人也散得差不多了。
他车就停在不远处,雨势越来越大,草地变得泥泞不堪。
钻进车里,前方挂着金离送的卡通吊件,是戴墨镜的史迪奇仔,一晃一晃好像在跳迪斯科。
发动了好一会还是无法启动,很遗憾,车应该是抛锚了。
更遗憾的是,伞也没有拿。
这附近不好打车,回家的路线也没有直达的公交。
他给拖车公司打了个电话,对方回复今晚前一定把车拖走。
挂了电话,没有别的办法。
开始的路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快一小时,淋了一路雨,终于看见出租车了。
到家时大衣全都湿透,衬衫粘在皮肤上,看起来好不狼狈。
佣人小心翼翼又充满担忧地问他:是不是被谁抢劫了?
家中一派欢庆的气氛,连厨房的磨砂拉门上都贴着“囍”字,显得他特别格格不入。
金离是在他到后十分钟迈进家门的,脸上带着浓重的倦色,估计是婚礼彩排累着了。
陈景明强迫自己不去看他,最后还是被人持续不断的咳嗽声吸引了目光。
他们从六岁开始就一起生活,对彼此的了解无人更胜。都不需问“你到底哪里不舒服?”陈景明往人额头上探了探,直接拿来了体温计,一测38.9度。
“你放心不会影响明天婚礼的。”
没事,反正也不是和我结婚。陈景明在心里说,嘴上只问:“我哥呢?明天就要结婚了今天他也不陪着你?”
“景辉哥还在看场地。”金离又忍不住咳了几声,陈景明就去给他倒水,温水,用的是他最喜欢的史迪奇杯子,去香港迪士尼的时候买的。当时陈景明看他拿了蓝色的史迪奇,自己就顺手拿了旁边粉色的差不多的款式。
“那是史迪奇的女朋友,安琪。”
陈景明不看《星际宝贝》,自然也不知道这个蓝蓝的小怪兽还有女朋友。他只是指着“情侣款第二件八折”的牌子说,“划算才买的。”
就着水吃了药,金离也不回房间,在客厅的沙发上盘着腿看动画,是史努比系列的电影。他对这些动画片都特别感兴趣,专业也是学的儿童绘本插画方向。
陈景明给他拿了条格纹羊绒毯搭在膝弯,看他杯子里水只消下去浅浅一层,又说:“发烧了要多喝水才好得快。”
“反正不会影响明天婚礼的。”
这是他第二次提起婚礼。
陈景明知道这代表着某种无助。他不禁想起一周前,也是一个普通的晚上,他终于开始路过学校,并抵抗内心逃离意志地跨进校门,处理他烂泥扶不上墙的学业。但生活也算规整起来,到点了下课,接受教授的问询,成叠的文书。然后他返回家中,看到金离在后院写生。
画来画去是那一片夹竹桃。
陈景明不喜欢这花,觉得很艳俗。他问金离喜欢吗,对方回答:喜欢谈不上,花一直在那里,看见想画就画了呗。
太阳已经落山了,浓郁的夜色泼下来,对着那个背影,陈景明最后问了一次:“小离,你真的可以和我哥结婚吗?”
对方闻声回头,表情是淡然的。
“可以的。”
这场婚姻对于金离而言更像一场明目张胆的掠夺。陈景明知道,他的哥哥陈景辉知道,他们的父亲陈舱知道。当然,金离自己也知道。
但他真的有选择吗?
父母过世后陈家的养育之恩是悬在他脖子上的枷锁,他被套住,锁牢。
所以当陈舱在餐桌上提起那份信托和信托下的那块地。
他说:“小离,叔叔也不想瞒着你,最近探测出那块地下很可能有稀矿,你能不能帮叔叔一个忙呢?”
这个忙就是和已经开始持股协成集团的陈景辉结婚,兑现那份以结婚为条件、只有婚姻双方才能取得所有权的地皮。
这本来是金离的父母谢鸿畅、金棘留给自己孩子的结婚礼物,最后变成一块筹码,一份人情。
“可以再陪我一会吗?”
金离没用什么力气,但被他扯住衣角的陈景明就此站定,没再移动。
“可以的。”
他回身坐下了,坐在床边,右手隔着被子把金离揽在怀里,像从小到大无数次做过的那样。
隔着被子他觉不出金离的体温,只觉得怀里的人是很薄一片,好像一松手就会消失。
退烧药的药效渐渐上来了,金离觉得眼皮越来越重。
其实他不想入睡,也不想做梦,只有陈景明身上淡淡的香水味是真实的,那是他送的十八岁礼物,清新明亮的海风气味。陈景明拿到时只说了谢谢,他还以为他不怎么喜欢。隔天人就要飞到外省上大学去了,机场送别拥抱时,金离认出他用了自己送的那款。嘴上不说,心里高兴。
等冬天来了,陈景明飞回来过寒假,金离又发现来的行李箱里多了一瓶崭新的同款。
关于陈景明的记忆太多了,一晚上肯定回忆不完。
他没能抵抗药物的催眠,缓缓入睡。
陈景明帮人细致地掖了被子,轻手轻脚地出了房门。
想下楼倒杯水,却被父亲叫住。
“景明,来一趟书房。”
陈舱见他进来了,摘下了眼镜,屏幕上的测绘图陡然模糊起来。
“什么事?”
“你又去小离房间了?”
陈景明在桌前的小沙发上坐下了,将衬衣扣子又解开两颗。
时间不早了,他很困,没否认也没肯定,只是坐着,目视前方。
墙上挂着一幅画,是很简洁的画风,蓝色的天空,蓝色的湖水,湖边坐着四个小人。
他不禁觉得金离好傻。
“明天之后就要注意了。”
他还是原来的姿势,一九零的个子在带有扶手、四四方方的小沙发里怎么也无法舒适,索性一动不动地干熬。
“知道了。”
陈舱似乎没料想到他这样直接的应和,本来准备的一番说理落空,只能干巴巴地补了一句:“延毕的事情也别太紧张,这次只要稍微用点心,是没问题的。”
陈景明几不可察地“嗯”了一声。
“我先睡了。”话音落地时人已经走了,顺便带上了门。
被叫醒时还是晕乎乎的,房间里脚步声不断。
金离一睁眼就看到一屋子人,离他最近的那个手里拎着他今天要穿的礼服,是花大价钱请了国际知名的设计师量身定制的,他只试穿过一次,是在设计师的工作室,陈景明陪他一起去的。
设计师助理热情地迎接了他们,又泡了两杯锡兰红茶,笑着说:“二位真般配。”
“您误会了,新郎不是我。”
陈景明率先解释了。
金离捧着茶杯,没过滤干净的几片茶叶漂在茶面上,如几具浮尸。
助理面露窘迫,气氛也一时有些尴尬,在成衣被拉出来展示时,才有所缓解。
“金先生,您试试吧。”
做工确实很精巧,暗纹是设计的水波纹路,成品在藏青底色下衬得如同一条暗流涌动的河。穿上身后,效果没那么明显,但还是非常可观。
陈景明在他走出试衣间时从米色布艺沙发上站了起来,他走到金离身旁,几乎是暧昧的距离,眼神毫不掩饰地上下打量,手似乎在感受材质,实际上借着旁观的视线盲区,在腰部逗留。
“很适合你。”
“金先生,时间有点紧张了,您看是不是尽快起来洗漱?”
金离起身时人晃了晃,吓得旁边一众人也跟着提起心。
家庭医生也到了,帮他测了体温,显示正常了。
这意味着他可以做一个合格的新郎。
等妆发完毕下楼,门外停着一辆蓝宝石色的宾利。
车窗缓缓下降,露出陈景辉的脸。
他和陈景明五官轮廓大致一样,但他的更深邃一些,不讲话时给人强烈的凌厉感。
“小离,早上好呀!”
一开口严肃感就消散了,不过金离也想过可能是说话对象的缘故,毕竟也不是没听说过这位景辉哥在公司开会时,对着一看就是新人代做的报告质疑了整整十五分钟,参会者统统如坐针毡,如芒刺背,最后以业务组组长主动出来认错为结局。
从此一战成名,全公司上下无人不知,这位陈家公子并非饭桶一个,而是铁板一块。
“早上好,景辉哥。”
若别人看到这对话场景,可能联想到兄友弟恭,但实在很难联想到这是即将参加婚礼的一对新郎。
不过金离并不排斥陈景辉,他比陈景明和自己都大三岁,虽然三岁足以构成一道不小的代沟,他们小时候在一起玩的时间也不算少,在他眼里陈景辉是一个还算靠谱的哥哥。
他们三个上的是同一所初中,在当地属于学费最高的那一栏。他和陈景明刚进预备班时,陈景辉已经在上初三。刚进去的时候要分班考,他们俩学习都不怎么上心,一齐做了吊车尾,分到了八班。陈景辉作为陈舱口中“是读书的料”,四年来从来没掉出过一班。
金离记得初中第一学期的寒假,赶上教改新政策,从下一届开始除了语数英,可以自选中考科目。他们才预备年级,还几乎什么都没学,自然还不能做出选择。但这也导致了各科都要先学起来,于是生物历史化学物理地理老师分发作业,练习纸如雪花飘飘。
过完年陈舱带着他们三个去扫墓,金离带的是自己挑的满天星,花瓣蓝白相间,远看像一片从天上飘下来的云。
他每回来都要自己在父母坟前多待一会,陈舱拍了拍他的肩说:“叔叔在停车那里等你,不急。”说完就要带着剩下的两个人先走了。
他调整了下坐姿,从抱着双膝,到盘腿坐着。
“妈,爸,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吧,其实我寒假作业还一个字都没写,如果你们在的话估计会骂我了吧?”
说出来后又觉得好笑,讲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同学怜悯的眼神,老师刻意的关怀,夜里常有的噩梦,他都没有说,但心里总是堵得慌,像堆了块大石头,他被阻塞在这里,被困在四年前火灾的阴影下,暂时没有逃脱的办法。
回去的车上也还是闷闷不乐,直到陈景明偷偷戳了戳他的手臂,又凑在他耳边讲:“小离,寒假作业的答案,我哥帮我们搞到了。”
在金离的成长历程中,陈景辉大致就扮演着这样的形象。随着协成集团越做越大,陈舱也越来越少回家,长兄如父,很多事情就由陈景辉出面解决。
他艺术生考试结束后,被两个学校同专业同时录取,有些摇摆无法决定。陈景辉那时已是常春藤名校的大三管理生,具体是哪一所他听过已经忘记了,但记得对方非常好心地帮他收集了好多信息,有公共渠道的什么学科评级,也有其中学生的评价,甚至考虑了之后如果出国进修何者更有优势。
然而在那次之后,他们再一次面对面好好聊聊的场景,变成了协商结婚。
陈景辉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进入协成集团,在基层磨练了没几年,获得大家一致认可,破格升入管理层。
晋升宴上,陈舱拿准机会提出了要转让部分股权给长子。不久后股东大会召开,程序也走过,陈景辉摇身一变,成了协成集团第二大持股股东。
陈景辉在一个傍晚突然出现在陈家老宅,他毕业后就搬去了市中心的公寓独居,上次回来还是过年家庭聚餐。
彼时金离刚下课回来,他当助教的艺术学院离家不远,就没住员工宿舍。
他手上脸上衣服上都沾着颜料,手拎着一副半成品,是油画棒涂的向日葵,花的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了,只剩下一点天空和草地没涂完。
一进门看到陈景明在沙发上坐着,手里拿着他买的动画碟片翻看。
“景辉哥?”
“小离回来啦?”
陈景辉着一身深灰色西服,带钻的袖口折射着光。他比陈景明还要高上两公分,这样一打扮就有了压迫感。
金离无端紧张起来,他有预感这次陈景辉这次回来的目的并不简单,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
“紧张吗?”
坐上车后金离就一直望着车窗外,避免和旁边的人有眼神接触。
“啊?”金离闻声扭过头,冲陈景辉笑了笑,“不紧张。”
确实没有紧张的必要。
结婚证早在几天前就领好了,领完当天就签了地块的转让协议以及婚前协议。金离不太懂,也不是很想弄懂其中细节。就只是坐在那里,等待一份份文件递到他的面前。
陈景辉却一份份地拎出来给他讲解重要条款,这条意味着你会得到多少转让费,这条的意思是即使离婚了,你也会得到一笔不菲的补偿金。
金离一边听着一边走神,窗外传来鸟鸣,他在想那是什么品种的鸟。
“小离?”陈景辉在他面前晃了晃手掌,“还有什么问题吗?”
金离摇了摇头,停在窗边梧桐枝上的灰毛小鸟振翅飞走,他在协议的最后一页签上自己的名字。
随着协成集团的蓬勃发展,成为江城数一数二的龙头民营企业。其实他们都很清楚,这场婚礼不过是为了堵上风言风语而已。
也正是出于这点,排场要大,每一道程序都要精心,让旁人看起来是一对青梅竹马日久生情,才能打消外界的疑心。
婚礼地点是城郊的一块私人草坪,尽管递发请柬时都做好了保密工作,车快开到大门时,还是有零星举着摄像机的人蹲守。
金离不知道车窗贴了单项膜,不禁有些慌张,本来维持着向窗外看的姿势也调整成了目视前方。陈景辉见状轻轻捏了捏他的手,随后拢住了。
金离以为他是做样子给外面的记者看,便任他牵着,还反手攥住了对方的手。
陈景辉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他们下车时已经到了不少宾客,江城商界叫的上名字的都收到了请柬,自然没有不来的道理。
离了车内暖气,金离不禁打了个寒颤。他烧虽然退了,人还是有点无精打采的。
他环视四周,想找到陈景明的身影,却一无所获。
肩上突然落下一点重量,抬头发现是陈景辉给他披上了自己的羽绒服。鼻腔内瞬间传来辛辣的木质调香气,是对方常用的香水。
“小心着凉。”
话音刚落,他们就被带着往准备室走。
陈景辉走在前面,他个子高步子迈得大。金离平时穿惯了运动鞋,今天换上皮鞋还不习惯,加上他本来就走得慢一些,逐渐跟得有点吃力。
昨夜刚下过雨的缘故,草坪还带着些湿气。他一个没注意踩在一块小石头上,脚下打滑,为了保持平衡人没摔下去,脚腕拧了一下。
痛感传来,他顺势蹲了下去,手轻轻揉着受伤的部位。
“怎么了?”
陈景辉见状返回来,人也蹲下了。
“脚扭伤了?”
金离点点头。
“先别动,我看看。”
说着他慢慢剥下对方的袜子,露出红肿的脚踝。
“痛不痛?”
金离又点点头,随后又摇摇头,“不过我感觉应该还能走,应该不会影响婚礼的。”
“先别想那些有的没的。”
这是出乎金离意料的回答。
“麻烦你去叫一下医生。”
陈景辉对站在一旁给他们领路的服务生说。
对方应下来后,拿起手机拨了个号,很快走开了。
他们现在待的地方是草坪的后方,旁边是一大片湖,离布置好的婚礼会场有点距离,加上不远处有一间小木屋,正好可以阻隔宾客的视线。
一直蹲着有点累,金离尽量不拉扯伤处,小心地坐下了。
陈景辉也坐下了,坐姿毫无形象,价值不菲的皮鞋上沾了几根青草。金离看不过去,顺手就替他摘了。
“谢谢小离。”
“不客气。”
气氛由此轻松了一点。
痛感还是若隐若现地从脚踝处传来,金离手掩在上面,时不时地要控制一下表情。
“等下看医生处理,如果还是走不了,就推迟好了。”陈景辉突然来了句。
“不用,应该可以坚持。”
这也是金离没预想过的对话,不得不说今天超出他预期的事情有点多。
“小离。”
金离应了一声,转头正好对上对方的眼神,他无端地无措起来。
“你坚持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以后不用坚持也可以。”
是吗?
心中的问句说出口变成一句意味不明的“喔。”
金离闪过刹那的错觉,好像他并不在自己与陈景辉的婚礼现场,此刻不过是一处再普通不过的片刻。陈景辉还不是什么协成集团的大股东,不是商界冉冉升起的新星,而只是帮他弄来寒假作业答案的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