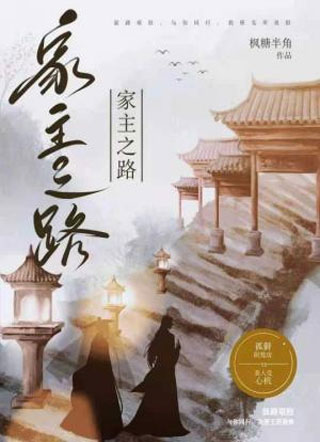
时间:2022-11-26 来源:长佩 分类:现代 作者:枫糖半角 主角:林飞白 赵永
“跪下!”
黄杨木做的拐杖往地上一撑,地面炸出一道惊雷,惹得祠堂内外的人心中一颤。
林飞白刚从宿醉中醒过来,头脑一片昏沉,他晃了一下脑袋,道:“不知飞白做了什么事让祖母如此动怒?”
何怀思头上戴着黑底红牡丹纹抹额,身上穿着一身深褐色对襟棉布长衫,脚上穿着一双黑色圆头布鞋,手上持着一根拐杖,用凌厉的目光审视着林飞白,语气严厉了三分,极具羞辱地说道:“你还有脸问,看看你那衣裳不整的样子,真是丢尽了我福州林家的脸!”
林飞白低头朝自己看了一眼,白色的外衫皱皱巴巴,腰带早已不见了踪影。心道,昨天他不过是和几个朋友一起举办结社活动,为什么会把自己弄成这幅样子?祖母最是重视规矩和礼仪,不管怎样,先过了祖母这一关再说。林飞白在脑海中思索一番,解释道:“昨日我与好友在林中小聚,一时兴起,喝多了酒,不想醉成这幅模样,的确有失礼仪。飞白绝不再犯,还请祖母从轻责罚。”
何怀思眉目一敛,质问道:“单单是喝醉了酒这么简单吗?我林家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不孝子孙!跪下,向列祖列宗谢罪!”
林飞白站在祠堂中央,感觉祠堂四面八方的风都向自己刮来,而他周身没有一处挡风的地方。他拢了拢外袍,说道:“敢问飞白究竟犯了何事,祖母要如此对我?”
何怀思刚要开口解释,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道:“老身耻于说出口!”
林飞白眉头一皱,心道,他不过是衣衫不整,仪表不甚规范,何至于让祖母发这么大的脾气,还不愿说出来,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猫腻。他再三请求道:“请祖母详细告知,飞白就算是死,也要死得明白!”
何怀思动了动嘴唇,却没有发出一个字。
站在一旁的林飞杰道:“祖母不愿说,我来说。昨日你在烟花巷狎妓,败坏林家的名声,你还敢狡辩!”
林飞白朝林飞杰觑了一眼,道:“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狎妓!”
林飞杰嗤了一声,他从怀中抽出一根腰带,凑到林飞白眼前,说道:“两只眼睛都看到了!今天早上,祖母和我一起去了花柳巷,亲眼看到你和烟花巷的妓女睡在同一张床上。你的腰带都是从那妓女身上取下来的,上面还带着脂粉气,你要不要闻闻?”
林飞杰是林家第三代长孙,也是林家下一任家主的预定继承人。林家家主向来有传长不传幼的传统。原本林飞杰作为长孙,可以高枕无忧,等待着自己的父亲寿终正寝,就从父亲手中稳稳当当地接过家主之位。可最近林飞白不知道给祖母灌了什么迷魂汤,得到祖母的翡翠玉如意不说,还数次被祖母夸赞。林飞杰气不过,总是等着抓林飞白的小辫子。好不容易看到林飞白犯错,林飞杰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次机会。
何怀思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气,又气又痛心道:“你马上满十五岁了,做出这样的事,以后哪个良家女子敢嫁给你!”
林飞白仔仔细细地将腰带打量一番,却没有接腰带。这条腰带的确是昨天系在他身上的腰带不假,可他昨日宿醉得厉害,压根不知道醉后的事。狎妓之事他定不能认,若是认了,他这一世的名声就彻底毁了。原本狎妓在大金朝不算一件大事,因为大金朝并没有禁止官民狎妓。自从花柳病从窑子里传开,狎妓就成了人人谈之色变的事,也为人所不耻。像林飞白组织的青云社,若是社员之中出现一个狎妓之人,那青云社会立马解散,再也组织不起来,以后也没有人愿意和狎妓之人来往。商场上只要出现一个狎妓的商人,其他商人就不会跟他合作,客商们也不会去他店里买东西,生怕染上花柳病。
林家世代经商,最是重视名声,历代家主都以严于律己著称,对家人更是严苛,绝不容忍家人犯一丝有损名声的事。若是犯了,必然严惩不贷。林飞白虽然没有把娶妻生子的事放在心上,也不能断送自己的经商之路。
他们青云社的结社活动甚是私密,除了已有的社员以外,从不携带陌生人参加结社活动。从福州郊外的密林到烟花巷尚有一段距离,林飞杰是怎么知道他宿在烟花巷的,还带了祖母过去,难道这一切都是林飞杰在背后做的局?那是谁配合林飞杰,把他灌醉,又把他交到了林飞杰手中。青云社的每一个社员都是他发展起来的,断没有背叛他的道理。他和林飞杰向来不对付,他必须冷静下来,不能着了林飞杰的道。
林飞白眼珠一转,道:“那妓女在哪?我要与她对峙!我没碰过她,她休要污蔑于我!”
林飞杰戏谑道:“你还想把她请过来,莫不是想把跟她的丑事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再做一遍。”
何怀思怒斥一声,道:“够了,审人就审人,你莫要说这些污言秽语来污了老身的耳朵,否则老身连你一起罚。养不教,父之过,弟不贤,兄之过。林飞白能做出这样有辱门风的事,你这个哥哥又能好到哪里去?”
林飞杰眼中一惧,连忙解释道:“祖母,你别误会,我不过是怕林飞白早就和妓女串好了说辞,沆瀣一气。林飞白是林飞白,我是我,祖母别将我们混为一谈。”
何怀思不屑道:“这个时候倒是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平时要你跟你父亲学学怎么管教府中众人的时候哪去了?”
林飞杰讪讪道:“马上学,马上学。”
何怀思朝祠堂内外审视一圈,掠过林家历代祖先的牌位,掠过祠堂墙上的家训,掠过祠堂外面的众人,最后将目光收回到林飞白身上,斥道;“来人,林飞白违反《林氏家规》第一百一十一条不得狎妓的规定,杖责二十大板。”
《林氏家规》总共七百二十七条,从治家、求学、经商等方方面面对林氏子弟进行了约束,是福州所有林氏子弟必须遵从的典范,也是林氏族长、林家各大家主、林家长辈用来惩罚林家犯错之人的蓝本。一旦触犯了《林氏家规》,轻则被林家家主施以杖行,重则被逐出林家家门,此生不能再踏进林家一步。
林飞白挺直了胸膛,道:“我不服!”
“哪里不服?”何怀思嘴角一撇,问道。
林飞白正气十足地道:“我并未碰那女子,祖母为何不给我机会让我跟那女子对峙?若是当面对峙,祖母自会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也能还我一个清白。”
林飞杰拿起厚重的木杖,往林飞白膝盖后面狠狠地挥下一仗,打得林飞白膝盖一弯,扑通一声,直接跪在了地上。林飞杰道:“跟这种林家败类、不孝子孙啰嗦什么!祖母舍不得打他,我来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还想抵赖不成!”
林飞白想要从地上爬起来,厚重的木杖又落到了背上。一杖,两杖,三杖......林飞白的背瞬间红了起来,钻心的疼痛从背部冒了出来,直窜到天灵盖。林飞白紧咬着牙关,不愿发出一丝喊疼的声音。
林飞杰见林飞白不喊疼,又加重了手中的力道。
一层层疼痛的汗水从林飞白的额头上冒了出来,木杖却没有打完。
“林,氏,家规有误,你们记错了林氏家规。”一字一句从林飞白的牙缝里挤了出来。
何怀思扬了一下手,示意林飞杰停下手中的木杖,道:“《林氏家规》七百二十七条,是你先祖父联合七大房长历经一个月制定的,林家众人都无异议,岂容你置喙?”
林飞白虚弱地说道:“《林氏家规》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若犯错之人所犯之事存疑,着林氏全族商讨所犯之事,一同决定对犯错之人处罚之策。祖母不是林家家主,也不是林氏族长,林飞杰也不是。我一再申辩我没有狎妓,没有违反林氏家规,你们不经调查,就对我处以木杖之刑,你们违反了《林氏家规》,你们是林家的罪人。”
因着林飞白是林家最小的孙子,母亲又对他的管教甚是严苛,所以林飞白自小熟读《林氏家规》,对《林氏家规》中的每一条家规都能倒背如流。他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家规驳倒伤害他的人。
何怀思的神情有一瞬间的恍惚,眼前这个人,天大的事塌下来了也毫无惧色,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谋取利益,俨然有当年林光启的风范。
林飞杰见何怀思陷入回忆中,深怕何怀思因为陈年旧事对林飞白网开一面,忙火上浇油地说道:“祖母就算不是家主也有管教你的权利,顶撞长辈,蔑视林氏家规,罪加一等,再加十杖。”
平常人打十杖就下不来床,打二十杖要去掉半条命,林飞杰一下子给林飞白增加到三十长,是想活活将林飞白打死。
林飞白质问道:“林飞杰,你还没坐上林家家主之位呢,就这么急着行使林家家主的权利,谁给你的胆子?你这么急着封我的口,这件事是不是你一手策划的?”
林飞杰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道:“你胡说什么,有错不认,还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我才没有你那么下贱,净跟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混在一起,跟你那下贱的娘一样!”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林飞白被林飞杰的话激起全身的逆鳞,他唰地一下从地上窜了起来,揪住林飞杰的领子说道。
林飞杰抓住林飞白的手,用力往外一甩,道:“你娘下贱,你也下贱,果然什么样的人就生出什么样的贱种!”
林飞白被林飞杰甩离出去,又嘶吼一声,朝林飞杰冲将过去,目光像是要将林飞杰撕碎一般。
林飞杰心中一骇,往何怀思身侧躲去,颤着声音说道:“祖母,你看林飞白这个样子,像是我们林家欠了他血债似的!”
何怀思斥道:“犯上作乱,目无尊长!来人,将林飞白给我捆起来,将刚才没打完的木杖打完,让他知道什么规矩两个字怎么写。”
祠堂外的仆人冲了进来,拦住林飞白的脚步,又用麻绳将林飞白捆了起来。
林飞杰见林飞白双手双脚都被束住,心中的胆子又壮了起来。他手持木杖朝林飞白走去,用力全身的力气挥起木杖,朝林飞白的背上砸了过去。
林飞白终是支撑不住,呕出一口血,倒在了地上。
他自小循规蹈矩,不敢越出家规一步,没想到这一次栽在自家人手里。这林氏家规他不遵守也罢。总有一天,他要让今天欺负他的人,全部血债血偿!
一个平静无波的声音从祠堂外传来:“母亲,杖下留人!”
一个头梳圆头低髻,身穿灰色对襟棉布常服,脚上踏着一双紫色美人蕉绣花鞋的妇人走了进来,周遭嘈杂的气氛没有掩盖她冷漠疏离的气质。她径直朝何怀思走去,走到距离何怀思三尺远的时候停了下来,规规矩矩地朝何怀思行了一个礼,道:“祖母,飞白纵有千般不是,到底是我的儿子,请你宽恕一二。我膝下就这么一个儿子,若是他死了,我晚年也没什么倚靠。”
何怀思脸上出现一瞬的犹豫。扪心自问,她对林飞白确实没有嫌厌到这种程度,况且林飞白以往的表现一向不错。只是这一次不知道被那女人灌了什么迷魂汤,做出这样不清醒的事来。何怀思正打算松口,就听见一杖木杖击打脊背的声音,林飞白彻底晕死过去。
赵清宁上前一步,抓住林飞杰的手腕,道:“不是叫你别打了,你没听到吗?”
林飞杰感到手腕异常地吃痛,表情瞬间扭曲在一起,他想挣开赵清宁的手, 却赵清宁不知用了什么巧劲,怎么也挣不开。林飞杰的脾气瞬间上来了,他凶道:“你算老几,轮得到你来管教我吗?”
赵清宁朝林飞杰瞥了一眼,道:“《林氏家规》怎么学得,背熟了吗?第十条家规上说的什么?”
明明赵清宁的眼神没有一丝波澜,林飞杰却不知怎得,感觉到了寒意,他勉强稳住心神,反驳道:“这关你什么事!”
赵清宁嘴角微微一扬,道:“《林氏家规》第十条规定,不得对长辈不敬。我赵清宁再怎么不济,到底也比你长一辈,你又是怎么跟我说话的?”
“你,你,”林飞杰被赵清宁怼得哑口无言,随即转向何怀思,抱着何怀思的手臂道:“祖母,你要替我做主,我都是听你的话才打林飞白的。”
何怀思用力一挣,睁开林飞杰抱住自己的双手,怒道:“够了,你做人能不能有点担当,退下!”
林飞杰闻言三步并两步退到了祠堂外面。
何怀思望着林飞杰的离去的背影失望地摇摇头,随即收回目光,对赵清宁道:“人你带回去吧。这次看在你的面子上,我饶他一命,终究是我林家对不起你。下次他再做出这等出格之事,我绝不轻饶他。”
“谢祖母,”赵清宁平静无波地应道,随即对下人吩咐道,“林虔,将少爷带回去。”
“是!”林虔毕恭毕敬地说道,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刚迈出门槛,赵清宁便对站在门侧的林飞杰说道:“还有,你嘴巴记得放干净点!我是林飞白唯一的娘亲,也是你林家明媒正娶的人。如果不知道怎么称呼我的话,多看看家谱。”
林飞杰咬了一下嘴唇,没有接话。
赵清宁眼神没有一丝波动,冷漠道:“你听到没有?要不要我再重复一遍?”
林飞杰敷衍道:“知道了,送别叔母。”
赵清宁面无表情地朝前面走去,林虔背着林飞白走在她后面,路过林飞杰时候,林飞杰俯身在林飞白耳边说道:“谁让你抢我风头的,我就是要让你尝尝被人打压的滋味。”
林飞白的耳边动了动,手指呈微微握拳状,眼睛却没有睁开。
走到林飞白的卧房前,赵清宁停下了脚步,她用手指着林飞白的床榻,吩咐道:“将人放下吧,去请个郎中来。”
林虔小心翼翼将林飞白放下来,因为红肿的背部先落到了床上,林飞白疼得嘶了一声,本能地蜷缩在一起。
赵清宁微微皱了一点眉头,道:“让他趴着。林飞杰打他打得狠,他现在还不能躺着。”
“是,夫人。是我疏忽了。”林虔拿来一个枕头,垫在林飞白头下,又慢慢地挪动林飞白的身子,让林飞白呈现趴着的姿态。
做完这一切,林虔立马朝门外跑去,边跑边在心里喊道:“少爷,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我这就去帮你请郎中。”
半个时辰后,林虔带着郎中走进了林府,穿过恢弘气派的前厅,穿过弯曲环绕的走廊,穿过孤高耸立的卧房大门,林虔终于回到了林飞白的床边。林虔道:“郎中,我家少爷今天受了杖刑,你快帮他看看,他身子骨可还完好?”
郎中放下称重的樟木药箱,伸手摸上林飞白的脉搏,闭上眼睛,慢慢地感知林飞白脉搏的跳动,片刻后说道:“气息微弱,这伤约莫伤及了肺腑。将他衣裳解开,让我看看伤。”
林虔听话地解开林飞白的外衫,从后面将林飞白的内襟摞起来,将林飞白的后背展示给郎中。林飞白平时光滑洁白的后背此刻布满淤青和杖痕,连平时古井无波的赵清宁看了都倒吸一口凉气。赵清宁道:“你好好治,不要计钱财。要多少钱从我林家账房里领。”
郎中压了压林飞白淤青的皮肉,说道:“少爷虽然伤得重,好在筋骨尚强,没有断裂。等老夫为少爷活血化瘀,少爷躺上一个月应无大碍。”
赵清宁点了一下头,道:“我知道了,等人醒了再告知于我。”
“是,送别夫人。”
郎中取出一瓶活络油,倒在林飞白的腰窝上,又慢慢向周围推去。
林虔边看边心生疑惑,问道:“伤筋动骨不是应该多休养才是吗?郎中你这样推背真的有用吗?”
郎中抬起头来瞪了林虔一眼,说道:“你是郎中还是我是郎中,你这么不信我,要不你来看!”
林虔连连摆手道:“不不不,我只是太过关心我家少爷了,请郎中莫要见怪。只要你能治好我家少爷,你打我骂我都行。”
郎中呵了一声,继续手中的动作。一刻钟后,郎中停下手中的动作,用手绢擦了擦自己的手,道:“好了,结钱吧。”
林虔咋舌道:“这,这就好了?”
郎中反问道:“你还想怎样?”
林虔看看郎中,又看看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林飞白,结结巴巴道:“不是,我是想问为什么我家还没醒?”
郎中叹了一口气,道:“且等着吧。今天是醒不过了。这段时间给他喂点清淡的食物,记得一天给他喂三顿药,一顿都不能少。要是少了,没准你家少爷就醒不过来了。”
林虔拱手道:“我一定谨记于心,多谢郎中,郎中慢走。”
送走郎中后,林虔转身就进了厨房。一连三天,林虔都按时喂林飞白喝药,为林飞白熬上一碗新鲜的药膳粥,想着等林飞白醒来,就能喝上热气腾腾的流食了。可是林飞白一直没有醒转的迹象,林虔只能一次次得将药膳粥倒掉。
第四天早上,林虔又端了一碗银耳莲子枸杞粥走进林飞白卧房。床上的人躬了一下身子,林虔手中的拖盘一晃,差点摔倒地上。林虔惊喜道:“少爷醒了,少爷醒了,我这就去通知夫人。”
林虔将托盘放下,往赵清宁的住处小跑而去。
林飞白想要开口制止,却发现自己的上嘴唇和下嘴唇之间结了一层薄膜,连开口都是艰难。林飞白扬起一只手,想要引起林虔的注意,却没想到连动全身的筋骨,身子像散架了一般,手也无力地放了下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林虔把赵清宁带了过来。
林飞白将双手作并拢状,却没有完全并拢起来,道:“恕儿子身体不适,不能给母亲行礼。”
赵清宁朝林飞白望了一眼道:“这礼不行也罢。”她朝左右两侧使了一个眼色,挥手道:“你们都下去,将门关上。”
林虔和府中众人都听话地退了下去。
屋内的光线一下子暗了下来,赵清宁的脸色笼罩在一片阴影中,她道:“如今这屋子里没有外人,你跟母亲说一句实话,你到底有没有狎妓?”
林飞白的眼泪泛上眼眶,道:“连母亲也不信我?”他本就生了一双极美的桃花眼,眼泪一盈满眼眶,倒呈现出几分可怜之状,让人不由得心脏一疼。
赵清宁用手敲了敲桌子:“好好地你惹林飞杰作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林飞杰的身份?”
林飞白篡紧了拳头,道:“是他口出恶言在先,我怎么能容忍他这样羞辱母亲!”
赵清宁眸光微动,道:“你跟他置什么气,不就是几句恶语吗?难道你母亲我不会自己报复回去?”
“儿子知道了!”林飞白眼神一暗,头脑也低垂了下去。
赵清宁话锋一转,说道:“你对母亲好,母亲心里是知道的,不过你要懂得收敛锋芒。”
林飞白解释道:“我那是为了林家的生意,谁知道林飞杰背后下阴手,手段这么下作。”
一旬前,林家就茶叶店的生意召开了家族大会,林家家主说林家的茶叶生意停滞了,除了卖卖老客,近一年来没有拓展过新的客商,问林家众人可有什么好的建议。
众人哑口无言,林家家主主动问林飞杰,林飞杰支支吾吾,半天后说可以跟官府合作,将茶叶供给官府。林家家主闻言思索了片刻,回道:“飞杰这个主意可是可行,只是目前我们没有相熟的官员,就是想送也送不出去。”
林飞白兴奋地站起来说道:“送不了可以请人来喝啊,我们可以把茶叶分为三档,每档用不同的水泡茶,给不同阶层的人喝。若是贩夫走卒,就给他喝井水泡的粗茶,只图他喝得勤,喝得多。若是乡绅士贾,就请他们喝泉水泡的好茶,讲究的是一个品质。若是王公贵族,就用新鲜的雨水泡陈茶,讲究的是茶叶的稀缺。茶叶也可以按照这三个档次来卖。”
林家家主拍掌道:“好,飞白的这个主意好,切实可行。今后茶叶店里的生意就按飞白说的这么做。”
林飞白的一番话赢得了林家家主林成业的赞赏,赢得林家人的一片叫好声,却引来了林飞杰深深的嫉妒。
赵清宁眼神一凛,道:“他才不管手段下不下作,把你的名声搞臭了的目的达到了不就行了。林家的生意还轮不到你来管。”
“我真的一辈子都没法接手林家的生意了吗,就因为我不是林成业长子,林光启长孙?”林飞白满是失落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