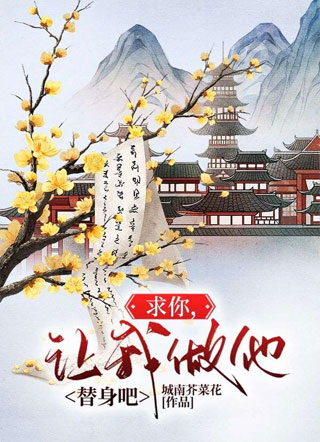
时间:2022-10-25 来源:寒武纪年 分类:古代 作者:取典长安 主角:符离岸 陆酩
“儿臣不敢。”
陆酩稳重如常,他微抬起上身,说:“既入了侯府,此人性命便由本侯担着一头。何况他虽名为质子,却是儿臣最信赖的幕僚,母妃再忿不过,也该顾念些儿臣的情面。”
淑太妃玉指点着他,冷笑连连:“好一个溧阳侯,翅膀长硬了,敢与本宫叫板了是不是?化周之策未定,保不齐就有变数在,这军权你拿不拿得稳还两说,此时就与本宫论情面,我瞧你是得意的太早。”
陆酩微微一笑:“北周归顺,不日将来使签订盟书,变法势在必行。”
与其说他在陈述事实,不如说是溧阳侯的政见若然。
大争之世,北周王室作为天子之邦,是最大的先朝。按例,无论哪国灭周,都应保留封地,许遗民聚居并因循周法,以示抚慰之德。
但陆酩不这么想。
从周王乞降的一天起,溧阳侯便极力主张在北周境内废黜旧政、请行新法。此主张不仅招致北周贵族的反对,在虞国朝堂也是引发一片哗然。
以淑太妃为首的外戚一党认为,他这是打算借此丰满羽翼,以期来日取而代之。
“是么?”淑太妃将怒气一敛,抚了抚髻上金钗,好整以暇道:“没有本宫在盟书上加盖玺印,这一关,你到了过得名不正言不顺。”
陆酩不怵,直言道:“变法之善,在能富国强兵。倘若母妃因妹妹不得回虞便横生枝节,只怕逃不脱一个祸国的罪名。”
淑太妃死死盯着他,突然笑起来:“吾儿天真,不知为母秉性。本宫行事,向来出于公心。”
出得承明宫,陆酩脸上殊无笑意。
“你,”他手提马鞭一指侍从,说:“去查一查商坊被淹是怎么回事。”
*
侯爷走后,符离岸独自窝在书房,写了大半晌文章。
今日不知怎地,午膳过后只觉腻腻的不消化。索性搁笔,携一卷策论至花园消食,未走两步路先教雪地湿了快靴,只好在亭台后寻了个僻静地更换。
“晏公子,这枝叶不好攀摘的,侯爷最是心疼不过。”
声音冷不丁响起,符离岸听出是管家,不动声色地撩下袍角。
这时候对面的人开口了,嗓音清越,有几分黄鹂啼啭的灵动,符离岸印象里从未在侯府听见这样的声音。
“我听说凤凰花生性喜阳,是咱们北周才有的庭栽。不想到了虞地也能见着这么大棵凤凰树,真是难得。”竟然也是个北周人。
符离岸陡然有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抬手摁低了掩在面前的松枝,寻声望去。
说话人是个唇红齿白的公子,月白大氅罩着玲珑身形,瞧着年纪还轻。想到传闻中所言,陆酩带回的清倌与莫如归眉眼更加相似,符离岸情不自禁地向前趋近了两步。
便是这一下,他踩到地上枯枝,惊动了不远处说话的两人。
“哟,公子怎么不多穿些再出来,天冷,仔细受了风寒。”管家撇下清倌,颠到近前嗔怪着道。
符离岸说:“房里地龙太足,身上燥得慌,出来透口气,一会就回去。”
管家道:“您且站在这别动,老奴去替您取件外氅来。这寒冬腊月的,冻坏了可怎么是好。”
符离岸微一颔首:“有劳。”
管家絮絮叨叨地走远了,侧旁的小倌清了清嗓子,主动上前见礼:“想必这位便是公子岸吧?晏平见过公子。”
他行的是周礼,本想借此拉近关系,怎知符离岸见了眉间却蹙起淡淡的褶皱。再一审视长相,像则像矣,只是画蛇添足地多了些精明算计,全无太傅大人身上那股超然气度,符离岸心头反感顿生。
没得辱没了。
符离岸便道:“既然到了虞国,须得学会入乡随俗,再行周礼只怕不妥。”
晏平听罢一怔,忍不住偷眼打量起眼前人——
早听说被遣来为质的公子岸是个奇人,分明出身北周,却无半点遵循周礼的自觉。才入虞国没多久,就攀上了溧阳侯这株高枝。
要说单是娈宠做的得心应手,晏平对他也不会有这么多好奇,毕竟烟花胜地也讲究一个人外有人。
可传言又说,这位质子岸学识过人,写得一手锦绣文章,从前在北周是明珠蒙尘可惜了了。
晏平对此嗤之以鼻。
王公贵胄怎样,书读再多又如何,到头来还不是和自己一般,也成了以色侍人的玩意儿。晏平幼年少学,不懂得明珠蒙尘是什么意思,但看到高岭之花跌落泥潭,他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潜生一阵快意。
只不过现在,这阵子快意随着打量逐渐消失了。
眼前之人衣饰普通,但自带一身贵气,光是眉宇间那股闲庭信步的从容,便是他无论如何都学不来的。
晏平懊丧地发现,高岭之花再如何沾泥染秽,仍旧是朵花,同自己这棵发于沟渠的狗尾巴草有着云泥之别。
好在,都是替代品。认真论起来,谁也不比谁高贵到哪里去。
“公子教训的是。”晏平敛眉恭顺,忽又展颜道:“要说入乡随俗这件事,自然还是公子体悟得更深。若还拘在北周的那些条条框框里,如何能哄得侯爷欢心?听说侯爷昨个儿快马加鞭从关外赶回,只为替公子庆生。啧啧,这样的好福气,想必费了公子不少力气吧?”
他有意把“力气”两字咬得很重,显尽暧昧。
然而符离岸神情漠然,恍若未觉:“让侯爷连夜赶回来庆生的人,不是我。”
晏平愣了下。
冷风谡谡刮来,掀开额发,露出一双无悲无喜的眼:“昨日不是我的生辰,侯爷他,记错了。”
不是公子岸的生辰,还能是谁的?晏平只诧异,若真像外界说的公子对侯爷有情,碰上这种事怎么还能如此淡定。
余光瞥见管家取了衣裳去而复返,晏平心念一动,回身牵住凤凰树枝,向着符离岸妩媚笑道:“侯爷一时怠慢了公子,您也莫伤心。秦楼楚馆有个规矩,凡是馆中要价高的角儿,都要把名字刻在树尖尖上,寓示着高人一等。”
说着,他猝然出手抢过符离岸束发的象牙簪,随意地在枝条上比划:“不如,我提前送公子个好意头。”
符离岸进逼两步,语声凉薄道:“放开你的手。”
晏平忽而面露惊惶,簪子“咣”地落在地上,手指并花枝颤颤:“公子这是要做什么,奴不过是要与您闲话几句故国风物呵。”
话音未落,见得凭空划过一道剑光,晏平连忙收手,仍是叫剑锋削去了半截衣袖。
他慌得匍地磕头不已:“侯爷......”
陆酩收剑入鞘,旋身时杀机毕现,连厚重的明光铠甲都弹压不住:“谁许你碰这树的,你也配?”
凤凰花树为莫太傅生前最喜,取意“叶如飞凰之羽,花若丹凤之冠”,喻示其凌绝枝头的勃然雄心。
晏平不知其中缘由,将那花枝拏在掌中,态度和妓子甩帕一般狎昵,无怪乎陆酩见了会生气。
他战战兢兢地道:“奴、奴只是在与公子叙话,谈及北周的花草一时忘情。可谁知公子嫌奴微贱,要拿簪子划破奴的脸......”
陆酩睨他一眼,嗤道:“公子什么身份,你又是什么身份,轮得着你陪着叙话?下回叫本侯看见你随意攀附,这侯府你大可不必再待了。”
晏平一咬唇,头埋得更低,不敢再置一词。
侯爷眼里没温度,绕过晏平解下披风,将符离岸整个纳了进去,手掌按在他后背肩胛骨上:“天儿冷,出来不知道添件衣服,还站在雪地里与人费这半天唇舌,冻坏了算谁的?”
陆酩弯腰捡起地上的象牙簪,仔细吹去上头的尘土,重新替符离岸束好发,道:“本侯赠予你的簪子,就这么轻易被人夺了,公子忒不讲究。”
披风上尽是侯爷的味道,符离岸拢在其间,眉眼显得过分服帖,似是感到了心安。
被那样的眼神望着,陆酩胸口攒涌的怒气一下消散了大半。
打从承明宫出来,他便有些气不顺,拐去京郊一趟,怒气愈发叠高了几层。陆酩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符离岸,谁知刚一入园就撞见了小人叫嚣。
陆酩拧眉道:“还跪在这里做什么?”
晏平落荒而逃,地上还掉着被侯爷挥剑斩断的半截袖。符离岸冷眼旁观,觉得今日的陆酩与以往似有不同。
但他已经习惯了不追问。
陆酩屈指蹭了蹭符离岸的脸颊,带着倦色解释道:“他是北周郡守执意要送给本侯的人,听说得了周王授意。情面难却,本侯带他回来,只为安周王的心而已。”
“周王?”符离岸诧然。
陆酩在披风下揽上他的腰,将人带近自己几分:“许是为了笼络,你的那位好王兄,最擅长这套,送一个来还不够么。”
话里糅进了些微挑逗意味,可符离岸的心思俨然飘到了别处:“怕是王兄觉得留我在侯爷身边,早晚会对北周不利吧。”
陆酩将头枕在他颈侧,嗅着淡淡的笔墨香气,眉头渐渐地舒展开。
“怎会?”溧阳侯笑语低沉,“公子惑心,早晚磨灭了本侯的志气,我看周王偷着乐还来不及。”
符离岸面皮一阵浮红,转而又将目光投向身侧的枝头,神情登时变得惘惘:“眼看就要春来花发,怎能轻易被人攀折了。”
放晴后的风都是轻柔的,让枝头堆雪轻飘飘、瀌瀌然地落,落在风领上,剔透折光,凝住了陆酩的眼神。
“阿离。”
“嗯?”
陆酩难得迟疑一回:“本侯,不是那等见异思迁的人。”
符离岸怔了怔,当即失笑:“侯爷误会了,阿离在说这凤凰花树,与您何干?”
陆酩一窒,重新把头埋回颈间,声音传来有些闷闷;“罢了,给本侯瞧瞧你今日又写了什么吧。”
望着符离岸清隽卓荦的背影,陆酩脸色渐暗。
他只是恍惚生出某种错觉,这府上的一草一木阿离都珍敛异常,不许旁人惦念了分毫。可唯独自己……
晏平过府一天一夜,符离岸连句同他置气的话语都没有。
哪怕一句呢?
“玄三,侯爷日间都去了何处?”
更阑人静时分,云将月掩,夜色浓沉似墨,符离岸凭栏而立,缁色锦袍与夜融为一体。
白天那黑影错他半步,垂手而立,见问稳声回道:“从宫里出来后,侯爷又拐去了城南的云商坊,踏勘完几条街的灾情方回。”
“云商坊?”符离岸有些意外,转身时不经意牵扯了某处,动作一滞。
玄三察觉异样,忙关切地问:“公子哪里不适吗?”
符离岸摆手,借着咳嗽偏头掩饰了尴尬:侯爷今日气不顺,连带着讨要的动作都比以往凶狠,投入时必得与他四目相对,不许自己移开视线半刻。
符离岸未解其意,却也陪他胡天胡地了一整晚,从临窗的须弥榻,到书房里的那张梨花大案。后来实在撑不住了,只得依附在侯爷肩上,猫儿似的直讨饶。偏陆酩最吃这套,那一叠声的“不要”可比什么暖情药都要管用。
下场便是,“身娇体弱”的公子岸如今小挪一步,都显腿软。
符离岸挡开玄三欲上前搀扶的手,忖着道:“云商坊不是北周商人聚居的民区吗,听说前阵子遭了水灾,王爷去那做什么?”
玄三改换手势,扶正腰间佩剑,郎声道:“属下也觉奇怪,所以询问了咱们在宫中的眼线。今日午后太妃召侯爷进宫,说是商坊近来不太平,这些天已经出了好几起周人滋事的案子。矛盾一日不调和,两国会盟的时间便一日无法确定。”
符离岸眉间一折:“怎么又扯到会盟上去了?”
玄三道:“外戚本就对变法一事心存抵牾,这回周人骚乱,更给了他们藉口。太妃认定周人对变法多有不满才寻衅滋事,此时举办会盟,绝非良机。”
玄三所言,符离岸心中会意。外戚的理由固然蹩脚,但若是存心作梗,再牵强的理由,他们也能找出附会的逻辑来。
会盟在即,符离岸决不允许任何阻碍变法的绊脚石存在。
“玄三,”他唤黑影上前,“替我传信给那人,就说我要见他。”
*
北周商人聚伙为患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城中聚讼纷纭。公子岸呕心沥血做的几篇好文章,皆在某些人的摇舌鼓唇间散作云烟。
“你看那些老周人,个个都那般凶悍,真要逼急了,不得跳起来反咬一口么!”
“你是说溧阳侯欲在北周推行变法的事吧?”
“可不。我觉着尚书令他们说的有理,北周的王道之治已经延续了几百年,你如今刚一收服,就要变革人家的祖宗礼法,搁谁身上不得乱。依我看,这当口可不宜火上加油,还是徐徐图之比较稳妥。”
“嗐,公子岸的檄文里不是说了吗,割痛剜疽、刮骨疗毒,贵在一个快字。总这么瞻前顾后,要拖延到何时。”
持方不一的那人呷了口茶,狠狠啐掉嘴里的茶叶末:“呸,弄臣走狗的话你也信?廉耻都不要了,还顾得族人死活!”
茶寮一隅,符离岸将这些刺心言论尽数听去,和着大碗凉茶一并饮下。
“公子身子弱,仔细叫凉茶一激,再激出什么毛病来。”
坐在对面的是个不修边幅的江湖郎中,方脸阔面,下巴蓄着一圈青黑胡茬,眉宇间颇见几分落拓不羁。
符离岸搁碗道:“我以为你要劝我收手,免得再叫人戳着脊梁骨骂。”
郎中捏起一粒花生米,扔进嘴里:“我劝,您肯听吗?”
符离岸摩挲着碗沿,迟迟不语。
“弄臣”“走狗”,这些早不算什么稀罕字眼,比这更龌龊的话符离岸也听过。
从入侯府那日起,人们打量他的目光里除了怜悯,便多了一丝鄙夷,不过是碍于侯爷,那鄙夷终究不曾过了明面。
直至符离岸真正站到变革派的一边,开始主张推翻故国礼法。对卖国求荣者的厌恶终于战胜了忌惮,人们选择用“弄臣”这样的字眼标记他。
为乞活命甘做宿敌手里的一把刀,那些人有多叹服他的词锋之犀利,就有多嫌恶他的心肠之刻毒。
“公子岸,乃天下第一薄情寡义之人,可怜、可憎、可怕。”如是评价,几乎成了对他的不刊之论,敌也好,友也好,皆以为然。
沉默的间隙,郎中把花生米嚼得嘎吱作响。
“公子身上的伤可大好了?我让玄三送去的药膏可还管用?”
符离岸回过神,微笑着道:“伤已无碍,亏得你的药膏。”
“要我说,公子本可以不挨太妃的十来鞭。”郎中嘴里犹在咀嚼,咬字有些含混不清,“她罚您是因为娈宠的传闻太过不堪,公子抵死不认也就罢了,何必担下这个虚名。激怒了太妃,您自个吃尽苦头不说,名声也做坏了。”
符离岸头也不抬,反问:“纵使没有太妃替我坐实,这虚名就不必我担了吗?”
郎中语一窒,搓了把后脑勺,瓮声道:“可您还受了刑……”
“一顿刑罚换一道嫌隙,”符离岸打断,“这买卖于我稳赚不赔。”
“您的意思,”郎中倏然瞪大了眼,“惹太妃动怒施罚是有意为之,为的便是让侯爷同情于您,继而与她离心?”
天枢阁里的果然都是通透人。
不过有一点他说的不对,符离岸从未把希望寄托在陆酩的情上,无论那情里有多少是爱,多少是愧。比起让侯爷同情,符离岸更倾向于用这种直白的方式,让陆酩感到颜面受损。
对于侯爷那样一个自尊心极强的男人而言,屈辱会比同情更容易催发出愤怒。他寄希望的,只有侯爷的愤怒。
符离岸低头又啜了几口酽茶。
“对了,让你查的事可有眉目?云商坊好端端地,怎么就乱了起来?”
提起这个,郎中便气不打一处来:“还不是禄蠹误事。民区被淹,按说只要拨钱拨人来赈灾便好。可偏偏工部与城防营久不对付,银子拨不下来,人也派不出去。京兆府尹是只老狐狸,觑着两头都无妥协的意思,索性做了壁上观。商人数月开不了张,生计一断可不就得乱么。”
符离岸有些不可思议,他问:“以虞法之严,怎容得王城根下出这种推诿扯皮的事?”
“今时不同往日啊,”郎中说:“有淑太妃在朝掣肘,侯爷许多事都难办。就说眼下这宗,修缮民区、重整商铺,哪样不是费人费钱的差事,侯爷再能耐,横不能凭空撒豆成兵、点石成金吧?”
符离岸从郎中的插科打诨里听出些微无奈。他沉吟片刻,拨弄着扣在桌上的茶碗盖:“我或许有一法,可破眼下的困局。”
听他说完,郎中脸上划过一丝隐忧:“公子此举,是否太点眼了些?以您目下的身份,实在不宜被推上风口浪尖。”
符离岸却道:“富贵险中求,非如此不得平复城中物议。”
闻言,郎中将玩笑神情一概敛去,口气随之严肃起来:“公子待侯爷这般尽心,该不会是动了真情吧?”
手指一顿,符离岸水波不兴地看向他,眼里没有丁点情意:“旁人不明所以,你总该知道内情。我对侯爷,是逢场作戏也是惺惺相惜,什么都有,唯独不可能是……爱。”
郎中似是松了口气,须臾说道:“那便好。只不过有件事还得提醒公子,您若真的帮侯爷解了此番燃眉之急,淑太妃以后只怕更加容不下您,上次是铁鞭,下一回就不定是什么了。”
符离岸笑笑:“不是还有你们吗?对了,我听玄三说,你前不久成亲了?怎不知会一声,我也好提前备份贺礼。”
郎中耸了耸肩:“干咱们这行的,脑袋系在裤腰带上,保不齐哪天人就没了。若凡事只管张扬,早晚要连累妻儿,何苦来?”
“玄五,”符离岸忽然动容,“让你们这些影卫跟着我两头瞒,实在抱歉。”
“公子您可别,哥几个跟着您,除了因为那位的缘故,也是真心实意想给北周挣出片新天地。还有,”郎中一脸嫌弃,“以后能别叫玄五了吗,听着跟王八似的。”
符离岸无声莞尔。
“记得低调行事,联络时切莫走漏了风声。”他不放心地又叮嘱了两句。
“知道了——”郎中拿起靠在桌边的幡子,一步跨出茶寮外,“时辰不早了,媳妇还在家等着我回去做饭,改日再听公子的教诲呐。”
符离岸望着他归心似箭的背影,没奈何只得叹息。
暮色四合,正是家家户户燃起炊烟的时候。符离岸出神地望着茶寮外一片茅檐低小,想起神医方才所言,冷不丁地陷入了一阵怅惘。
曾几何时,有个人也这样等过自己。只可惜,旧宅不复,那个让他归心似箭的人,也已经不在了。
符离岸低头抚上腰间荷包,璎珞已经被他摘了,只剩银色蚕丝缀着月白色绣囊,上面墨线织就的青松苍劲有度,恰如君子当年,遗世独立。
三日后,一则消息传遍了晋稷城。
秭下学宫三百学子自发来到云商坊赈济灾民,打着“为生民立命”的旗号,阵仗摆得十分浩大。
虞国尚武重军功,但对文治亦尊崇有加,能入秭下学宫的多半是官宦人家子弟,此事一出,顿时在朝堂乡野掀起了轩然大波。
“秭下学宫向来只关心著书立说的虚事,什么时候也热衷于这些俗务了?”是夜,陆酩看过奏报,合了折子,手指落在封页上。
老管家日间打听消息归来,亢奋之情溢于言表。
“都是公子,借着论战的名义切磋学问根本,凭一人之力把那起子老学究辩得满地找牙,恨不能立时三刻变成哑巴,才不至于被人笑话词穷呢。”
老管家说得唾沫星子乱溅,陆酩瞥了他一眼:“你好好说话,什么论战,什么学问根本?”
老管家赧然一笑,旋即又绘声绘色地描述起,公子岸是如何以一当十舌绽莲花,将“治经世之学”说得掷地有声,令四座拜服;又是如何说服诸生将为生民立命的口号付诸实践,劝动其往云商坊中,修缮房屋、捐粮捐物。
“他做这些,都是打着公子岸的旗号吗?”陆酩蹙眉问,心说未免也太招摇了些。
管家忙说:“公子机警,如何想不到这点。论战时他没有暴露身份,却化名了山松先生。说来也是个巧宗儿,那日的看客不识得公子,直说公子有惊世之才,好比山中松柏有仙骨,是个小神仙呢。”
虽知有夸张的成分在,陆酩听着仍是不知不觉勾起了唇。
“小、神、仙。”
陆酩将这三个字反复咂摸了几遍,似乎真有点齿颊生香的意思,“亏他想的出来。要是本侯没猜错,这群学生里还有工部尚书家的公子吧?”
“岂止,”老管家扳着指头数,“工部尚书的幺子、城防营统领家的长孙,还有京兆府尹的亲侄儿。得,齐活了。”
老子唱戏,儿子拆台,就连精通兵法的溧阳侯也不得不感叹:这招釜底抽薪玩得真是巧妙。
“看来我朝官员个个教子有方,当真可喜可贺。”陆酩情不真意不切地称赞一句,转而又道:“既这么着,咱也不能含糊。传本王钧令,学生义举理当嘉许,给几位大人府上送块牌匾去,就书——青出于蓝——几个字,聊表本侯激赏之意。”
老管家憋笑应完,“小神仙”正好跨门而入。
“侯爷,府里的账都清完了,还请您过目。”
陆酩而立之年不曾娶妻,家中一直缺个管事的主母。自打符离岸入府,一应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陆酩越瞧他,莫名其妙瞧出了几分贤妻的影子。
“过来。”略显昏暗的屋子里,符离岸听出侯爷的声音有些喑哑。
他不明所以,走近案前刚要点灯,忽然被人捉住手腕,跟着又叫一股强力拽了个天旋地转。
“开始替本侯当家做主了,嗯?”陆酩一语双关,符离岸眨眨眼,正要解释,却遽然一下被堵住了嘴。
陆酩吻住他,近乎贪婪地掠夺着那一副唇舌,符离岸要动,陆酩偏要圈住他,就圈在自己怀里。
神仙也好,凡胎也罢,都是他的。陆酩不容许他逃,也不容许旁人多觊觎一点。
因为喘不上气,符离岸隐约有些目眩神迷。窒息感让他误把陆酩的怀抱当成一张捕网,恍惚间竟有了自己是只猎物的错觉,这让符离岸觉出危机,却又深谙自己的无能为力。
“侯、侯爷,”唇齿稍稍分开一点,符离岸终于抓住机会推开陆酩,喘息着道:“你、你压着我了......”
陆酩低头看了眼,用舌尖抵了抵唇角伤口,猝不及防地抓紧他压在身下的另一只手腕,剪过头顶。
“好一个伶牙俐齿,小神仙名不虚传。”
符离岸垂眸,纤长的睫毛覆下一片阴影,他轻声说:“阿离擅作主张,请侯爷责罚。”
陆酩不错眼地看他许久,眼底情绪翻涌,讶异、狐疑、警惕,逐次闪过,最后却是化作一声长叹。
“你可知此番做了出头鸟,往后会成为多少人的眼中钉?本侯未必次次都护得了你。”
符离岸摇头,抵着陆酩的胸膛,一字一字道:“阿离不想一辈子躲在侯爷的羽翼下。”
陆酩露出个疑问的神情。
符离岸深吸一口气,抬眼与他对视:“阿离斗胆,想与侯爷一世并肩。”
心头咯噔一下,陆酩依稀记得,这句话他似乎也曾追在某人身后说起过。
“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陆酩胸口震动,漆黑的眸里瞬间褪去欲望,只剩下沉甸甸的注视。
符离岸平静地抬高下巴,那被润得泛红的唇半张。他拉低陆酩的脖颈,选择用亲吻代替了回答。
“本侯从前竟不知,阿离原也是个有志气的。”陆酩的呼吸濡湿了符离岸的耳,热浪一般的鼻息打在里面,烫得符离岸脊背发麻。
他把问罪的话说出了情人间絮语的味道:“你胆敢欺瞒本侯,”顿了顿,声音伴着力道加重,“当罚。”
符离岸闷哼一声,酥麻的感觉遍及四肢百骸,话音瞬间有些破碎:“阿离......知错......”
陆酩抚上他眉眼,指尖流连过唇心,落在喉结处的小棕痣上——画中人的相同位置,也长了这么一颗痣——陆酩总会被诸如此类的巧合淆乱了神志。
巅峰过后,他重新躺下去,与符离岸耳鬓厮磨:“但今日,本侯又复得了一件宝贝。阿离戴罪立功,本侯定要好好赏你。”
为褒奖公子深明大义,第二日清晨,溧阳侯便吩咐管家去库房挑两匹上好的蜀锦来。
“做衣裳?”符离岸好笑,“又不是小孩子了,哪有用衣裳做奖赏的?”
侯爷由着丫鬟替自己整理朝服,等到加冠时忽然扬手止住,示意符离岸来。
“衣裳自然算不得奖赏,”陆酩微微垂下颈,让符离岸将珠冠束于发心,方与他抵额,噙着笑道:“本侯只是想让阿离打扮得体体面面地,参加今年的抡才大会。”
抡才大会?
符离岸怔愣住,眼中闪烁着难以置信的光。
立春抡才是虞国士林一年一度的大典,也是晋稷孟春月最大的盛会。举凡能在抡才大会上语出非常的士子,往往能够一举成名天下知。可以说,立春的这场抡才大会,是每个志学之士都梦寐以求的盛典。
符离岸视名利若无物,却无比渴望在如此重大的场合推举自己的主张,他万万没想到,溧阳侯竟然主动开了这个口。
陆酩见他神色怔忡,笑道:“怎么,高兴傻了,还是不乐意?”
“侯爷,”符离岸斟酌再三,还是道:“我为藩国质子,照规矩,是不能与人论典的。”
“事贵从权,人贵机变。规矩若把人困死,就到了该变或是改废的时候。”陆酩词严理正,像是浑然忘了前两日他还要人好生守规矩。
符离岸不再推辞,他撤后半步,掖手过顶,长长一躬:“阿离,谢过侯爷。”
“对了。”
陆酩待他谢完,方将人扶起,说道:“今日城郊鱼龙灯宴,苍梧军中若无急务,待散了早朝,咱们也去凑个热闹好不好?”
鱼龙灯宴么?符离岸面上带笑,心思却逐渐下沉:“那不是得经过云商坊?”
陆酩只当他还在为周商作乱的事担忧,遂不走心地宽慰道:“本侯已经严令城防营加强云商坊四周的卫戍,阿离不必忧心。”
目光微闪,一个计划在脑海里悄然成形。
符离岸将唇弯成刚好的弧度,一颦一笑都是温顺,他袖着手道:“阿离听侯爷的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