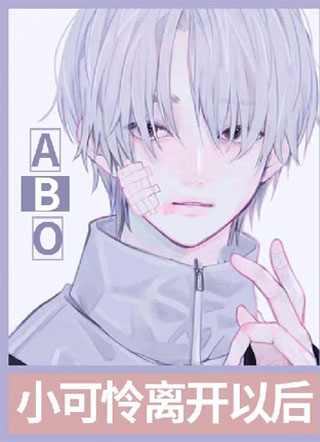
时间:2022-07-19 来源:书耽 分类:ABO 作者:钱途无量呀 主角:靳赫铭 白攸
但靳赫铭没有动。
男人只是张着一双眼,诧异万分。
他盯着座上面色陡然转白的青年,视线交叠间,两人俱是错愕。
一个惊,一个恐,僵持不下。
司机的刹车踩得极缓,悠悠地滑出去老远。这辆特地从高荣车行租去毕县乡下的车,他开得还不算顺手。
不仅如此,车上长时间的低气压,也使他胆战心惊。
“先生,我们到了。”
司机知道后座的靳赫铭和白攸当是又出事了,他深吸一口气,嗫嚅嘴唇,终是昂起脖子梗着头,如此提醒。
靳赫铭回神,未答司机半字。
他在座位上坐好,敲了敲车窗,像是在责备司机怎么没开过去,开到李祥如的祖宅前,怎么在这儿就停了。
而那样的声音,男人敲打玻璃窗的闷响,砸在白攸的心里,使他身形一怔,焦躁地捂住了耳朵。
心惧难安,好似热夏阵雨前轰隆隆的雷鸣。
“啊——!”
白攸沙哑着发疼的嗓子,无端地吼叫,听得司机与靳赫铭俱皆一颤。
男人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白攸身上,他的手刚刚抬起,还没碰到白攸,孱弱的青年就疯乱起来。
白攸抢着想要打开车门下车,手指扣在弹簧柄上连拉了十几次,“蹦”地一下,九球进洞,车门失锁打开,白攸整个人都猝不及防地摔了出来。
他的额头磕在了硬梆梆的水泥地上,撞了一嘴的石沙,没有丝毫停顿,青年紧忙爬起来就走,逃命一样地取路离开。
白攸根本就不知道李祥如的祖宅在哪儿,但走上桥,迎风就飘来了多戚的哀乐,像是顺着潺潺的流水送来了可贵的指引。
李祥如的乡下祖宅在荡河以南,司机把车停在距那儿最近的一条大路上,至于往南向里,那都是村里人一脚一脚踩出来的小路,连脚踏车都难走,更何况是汽车了。
再说司机停的这位置,同样聚了不少车,似乎也是奔丧来的。
靳赫铭看着白攸跌跌撞撞跑出去的身影,手掌在青年坐过的座位上重重地一揩,而后放到鼻下深嗅,隐隐约约还能闻到那淡淡一缕的玫瑰花香,混着缭绕的奶味儿。
如果说Alpha的信息素是压制,那Omega的信息素便是诱惑。即便为了防止被与之标记在一起的Omega控制,靳赫铭残忍地割掉了白攸颈后的腺体,有效地阻断了白攸大量信息素的喷发,但Omega渗出的外液中仍然会残存微量的信息素。
这些微量,对Alpha来说,也相当致命。
尤其是最近白攸怀孕,微量玫瑰花的芬芳,被日益渐盛的奶味催得慢慢浓郁。
这是Omega的身体应对生殖而形成的保护。孕期的Omega,情绪十分不稳,需要伴侣Alpha长时间的大量的信息素抚.慰。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Omega会控制不住地分泌更多信息素来勾引自己的Alpha。
现代医学将这一过程中Omega分泌的信息素称之为:孕素。
孕素的典型特征就是伴有挥之不去的奶味儿,而这样的味道,Omega自己或是其他人都闻不到,专门特供搞大他肚子的Alpha。民间有人会用这种方式来给未出生的胎儿做亲子鉴定。
宋友梅提醒过白攸孕素的事,但白攸觉得他的腺体都没了,就算有孕素,估计也不会太浓。直到他听到靳赫铭有意无意地说起了奶味儿……
如果让他知道我怀了孕,非要他的信息素才能好过,才能舒心,那我的下场可以想见了。
曾经靳赫铭算准了白攸的发情期,在青年像条饥渴的母.狗般发疯,哭着求他的时候,男人以保护Omega现阶段不宜发生特别关系为由,将人关进了Omega护理中心的禁闭室。
暗无天日的三天,每分每秒都是煎熬。
白攸按程序穿着信息素隔绝服,外面套着拘束衣,被捆在床上打针。镇定剂与抑制剂轮流伺候,他的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都是针眼,嘴里接着呼吸机,哭得眼泪都干了。
他空落落地睁着眼,拼尽全身最后一点儿力气,绝望地向男人点了头。
屈服。
他愿意放弃腺体,愿意马上手术。
“攸攸,好乖。”
白攸闭上眼之前,听到的就是这句“攸攸”。
哼,攸攸。
……
靳赫铭敏锐地闻着自己的手指,上面有白攸留下的气味。男人伸出舌头了舔,眼神深暗,似乎冥冥之中有了一些猜测。
他的白家小少爷可是0.01%的极优Omega,都要了两年了都还没个开花结果的动静,会不会如今有什么变化呢?
那可是他等了好久的游戏啊,用来祭奠他未出世的妹妹,最好不过了。
男人的心情一下大好,昂起头,用猛兽一样的目光,望着不远处桥上的青年。
他忽然问起司机:“我是不是该把他接回来,找个医生给他看看?他要是疯了,那可就没意思了。”
司机不明白靳赫铭为什么一下子又愉悦起来了,他愣了老半天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倒是男人像突然想到了一些事。
“他到哪儿了?”
“我给攸攸,给那死掉的老家伙送的这份大礼,千万别迟了。”
“到了?”
“到哪里了?”
王莲珍的眼饱浸泪水多日,现已睁不开了。原先她的眼神就差,如今丈夫一死,干脆便瞎了。
老太太花甲年岁,老态龙钟,瘦如枯竹的两条腿勉强撑着上身的空架子,被一左一右的两人扶出来,东倒西歪,好似一个虚弱的不倒翁。
谁都在猜她也活不长了。
王莲珍虽没见过白攸,但和白家关系匪浅。
白攸的母亲贺简嫁入白家,从贺家带过去的就是王莲珍。贺简常常“珍姨、珍姨”地喊她,叫得王莲珍心里尤其高兴。
贺简嫁到白家,嫁给白攸父亲白溥松的第二年,王莲珍就暗戳戳地和白家的园丁李祥如好上了。
李祥如和王莲珍是老乡,便直接带人回家结了婚,而后又在渝川毕县县城住了不少年,直到他们的儿子李茂离家出走,再无音讯——
两人伤心欲绝,辗转反侧之下,李祥如重回S市继续到白家当园丁,留王莲珍一个人在县城生活。李祥如当年娶王莲珍时答应要对她好,再回白家后,时不时就会给王莲珍寄钱。在他没有中风瘫痪前,李祥如确实是没让王莲珍吃一丁点儿苦。
只可惜后来……
祖宅的大门外才刚传话来说他们千等万等的那城里少爷来了,尚在里屋歪着的王莲珍就急急忙忙地让人搀她出去。
先前她已遣人给到车站接人的两个弟弟打了不少电话,问他们可看到小少爷了?小少爷可到了?但白攸却不是从高荣到毕县汽车站的,而是一脚就到了李祥如的祖宅门口。
白攸在前面走得快,好似后面有狼有狗在追,故意同靳赫铭拉开了不少距离。
他顺着高音喇叭举放喧鸣的哀乐找,摸到门前沙哑着嗓子问了一声就得以笃定。
果然是这里。
从外头往里瞧,三面围墙两个晒场四间矮屋并一幢二层老楼,李祥如的乡下祖宅还算气派。晒场上搭了两顶彩帐篷,一顶给和尚诵经吵得人头皮发麻,一顶筵席齐备放着不少空桌。亲戚邻居走来走去,一堆人全挤在一起或哭或笑。小孩儿穿梭乱跑,少年不识愁滋味地大喊大叫,吵得气氛更为喧闹。
王莲珍颤颤巍巍,从那幢二层老楼到四间矮屋,步履蹒跚地来到了白攸面前。
她伸出手,止不住地胡乱摸索,最后如同抓到了一块冷玉,力道极大地捏到了白攸的手。
王莲珍瞎着眼朝白攸面前凑,费心巴力地想要看清眼前的人是个什么样,但却于事无补。
她又想哭了。
“白……”
王莲珍嗓中一顿,神色尤紧,好似恍然大梦,顷刻便又回到了那时她在贺家、在白家的日子。
她喊白攸:“小少爷,真的是小少爷吗?小少爷来了?小少爷来了!”
王莲珍的眼中又渗出了泪花,一双手控制不住地在白攸的身上摸,有几处碰到了未消的淤青,疼得白攸暗暗龇牙咧嘴。
白攸禁不起王莲珍的这般热情,也受不住左右人全拿火辣的目光瞧上他。
和尚的经不念了,亲戚邻居不走了,小孩儿也往他这里凑。
一地静得出奇。
所有人都在看他,看这大城市里来的小少爷,听说还是个Omega,自然更是千金般地娇贵。就说他这穿着西装的漂亮样,阴柔白皙的脸上满是温柔,举手投足间又很有涵养。
人人都在交头接耳地谈论起白攸,谈论起这位李家不远万里而来的贵客——
好是好,就是妆化得有点儿浓,惨白的一张脸上毫无血色,难不成城里的小少爷都在流行这样的派头?
众人费解,白攸低头,更加遮遮掩掩,生怕被人看出那些伤痕的端倪。
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除了一遍遍告诉自己遭受过男人怎样的暴虐,毫无用处。
告诉别人也好,被别人知道了也好,谁又能帮得了他呢?说不定还会惹恼了靳赫铭,给那个人带去不必要的麻烦。
来时,靳赫铭不就扬言要对阿苑不利吗?
阿苑……
是个好孩子。
白攸默不作声地跟着靳赫铭赶路,阿苑一有空便会问候白攸。他心里担心靳赫铭将白攸带走又会变着法子毒打他,他担忧白攸回不来。
“哥,你给我个地址呗,如果三天了你还不回来,我就去接你。”
白攸没有回复阿苑。
靳赫铭提醒过他,他和阿苑的距离了,他就不该再不识好歹。
靳赫铭的底线是什么,他不必用阿苑试探。
白攸在李祥如的祖宅前干杵了半天,他回神回握王莲珍的手,十分勉强地想要扯出一个笑容,可到底只是平淡如水地对王莲珍说:
“不用叫我小少爷,我已经不是了。叫我攸攸,攸攸就好。”
他自己说到“攸攸”时还会不舒服,但一时半会儿又想不到其他称谓,只能强忍不适,如此将就。
白攸的嗓子早坏了,话一说多便会起痰不舒服,沙沙地难听。
王莲珍尽管眼睛瞎了,但耳朵却很好。虽然她先前没听过白攸的声音,可此时也觉得小少爷说话不太对劲。
“小少爷,你的嗓子怎么了?”
王莲珍还是改不了口叫“攸攸”,不知为何,白攸竟然松了一口气。但王莲珍接下来抛出的这个问题,又教他紧张,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我、我……”
白攸吞吞吐吐,把头埋得更低,垂眼看到自己腕上擦的粉底都快要蹭光露出那些青紫了。
他正踌躇着,忽然身后就亮起了那道既熟悉又害怕的声音。
“感冒了。”靳赫铭姗姗来迟,一出现就揽过白攸的腰不再使他逃脱,他替白攸遮掩道:“季节交替嘛,攸攸睡相不老实,感冒了鼻塞,所以说话声音才会怪怪的。”
靳赫铭搂着白攸,凭借高大的身躯抱住一个瘦弱的Omega还算绰绰有余。白攸对靳赫铭与他故作亲昵缱绻的丑态万分厌恶,在他怀中挣扎着就要离开。
男人感觉到了白攸比于车上变本加厉的反抗,强行将人拥得更牢、更紧。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就咬起了白攸的耳垂,说话的声音轻得只有他们才能听到。
靳赫铭说:“小少爷不会是想在一直挂念你的老仆人灵前丢脸吧?让他躺在棺材里也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好不好?”
明明上一秒还在他的耳边说着威胁、勒令的话,下一秒就忽然变了颜色,脸上露出温柔缱绻的珍爱,一边细密地在发间曼妙亲吻,一边恬不知耻地当着众人的面说自己是他心尖儿上的人、唯一的爱人。
呵。
男人的虚伪、做作使白攸分外不适。
他被强行夹在靳赫铭的怀中,忍耐着对方的“深情演绎”。
人群率先感到这个突然出现的,身材高大的Alpha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场。已经互相完全标记的Alpha和Omega,他们的信息素通常只为双方服务。但靳赫铭对白攸浓浓的侵占欲还是在众人眼中落下端倪。
“啊!”
短促的一声呛噎,白攸的瞳孔骤缩,鼻尖盈满凛冽的松涛。他困在男人的臂弯里,犹如顷刻被关进了精心为他编织的牢笼。
而他的身体却与他抵触的心绪背道而驰,一味地贪婪、一味地甘之如饴。
是肚子里的宝宝在闹着要父亲吗?
他还没见过外面的花花世界,甚至都还没完全成形,就已经能够通过爸爸,向他素未谋面的父亲撒娇了吗?
这样的想法使白攸的背上豁然惊出了一层冷汗。
他惶恐地睁大眼,指甲掐得嵌进皮肉,死死地克制着,不想被靳赫铭看出一丝异样。
咬紧嘴唇,白攸的双肩在靳赫铭的视线里显而易见地缓缓塌了下去。
他再一次向男人屈服了。
靳赫铭无非是在无声地要求他和自己一起,在外人面前在外面假装,什么喜欢、什么爱、什么天作之合、什么至死不渝……
就算白攸心知肚明这些、那些都是假的又能怎么样?他不是还得陪靳赫铭一同演戏。
深情演绎,演绎深情。
都一样。
委屈和难过打碎了全往肚子里咽,白攸望着眼前探问好奇的人们,低下头说:“嗯,他……他是我的Alpha。”
他们都以为白攸低头是腼腆、是害羞。
来自靳赫铭的威逼并没有因为白攸这样一句不算清楚的话结束,直到白攸如同鼓起了所有的勇气“坦诚”。
“三年前,他救了我,之后也帮了我很多。是我先喜欢上他的!他也很好地回应了我那样的心情。我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我很喜欢他,他对我……也很好。”
半真半假。
嗓子却是灼烧般的疼。
三年前,他和靳赫铭刚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刚刚成为靳赫铭情人的时候,他满心欢喜真的将这套说辞信以为真的时候,每每靳赫铭领白攸出去,他说起诸如此类的话,可谓倒背如流。
后来,他就不说了。
后来,他就只能在男人的命令下才得以稍稍表演了。
他喜欢靳赫铭吗?
这样的问题,不如多问问:Omega到底是喜欢Alpha,还是喜欢Alpha的信息素,又或是被标记后不得不借种繁衍完成生而为人的使命。
就算再怎么讨厌五谷杂粮,反反复复庸人自扰地去想人为什么一定得吃饭呢,但当饥饿、情欲这样的生理本能轰然来袭时,那样的情感该称之为喜欢,还是其他的什么呢?
男人的信息素满意地变调了,好似激越滚烫的重金属转而变成了意蕴悠长的十四行诗朗诵。
“攸攸善良、美好,像个天使一样。”靳赫铭毫不吝啬对白攸的夸赞,饶有兴致地轻抚他的发,其实心里在骂他白痴也说不一定。
男人抬起白攸的脸颊亲昵,扣着他的手,继续向众人说起“他心里的白攸”。
“攸攸一听说家里以前的长辈过世了,连忙哭着就要我送他过来。就说在我们来这儿的一路上,他也在我的怀里哭了好久呢。我家小孩儿爱美,一边哭一边又嫌弃满脸的泪痕是不是不好看了,还特意让我停车,他找人重新装点了一下。”
连小少爷脸上的妆浓,靳赫铭都一并解释了。
一句“我家小孩儿”,搭上他调侃的轻快语气,言辞间自然漫过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溺爱。
他一个人唱戏还不够,非要拉上白攸。
“是吗?攸攸。”靳赫铭邀宠似地问。
白攸只得配合演出,“是、是……”
靳赫铭奖励般地揉他的头,形同对待一只乖乖听话的狗。
王莲珍将靳赫铭和白攸的话全听了去,她对白攸如此挂念李祥如倍觉感激,心间不经一恸。
“小少爷……少爷!老头子他何德何能,能让您这么费心啊?他去S市后,好多次打电话回来都跟我说起您。他一直都把您当成他的亲生儿子一样看待!我虽然没见过您,但也知道简小姐的孩子一定又漂亮又大方。”
“少爷是Omega,千金娇贵,生来就是招人疼的。现在您又找到了一个对您这么好的Alpha,老头子他、他在下面……应该安心了啊!安心!”
王莲珍颤颤巍巍,酸涩的泪水从她糜烂不开的双眼里渗了出来,盖在最上面的眼皮不停地翕动,仿佛拼尽全力想要睁开似的。
她也想看看这个孩子,好好地看一看简小姐和白先生生的孩子长得有多可人。
左右搀王莲珍出来的人拿来面纸给她擦眼泪,都劝她快止住泪水,再不能哭了。
王莲珍控制不住,双手抖得更加厉害,“少爷!少爷!您来看老头子,您能来看老头子……我替他、替他……”
她说着说着就要下跪,白攸心头一惊,匆忙托起她的手,扶住了王莲珍身子的下倾。
白攸受不起王莲珍的大礼,对渝川乡下丧葬的繁文缛节不甚了解,颇是不解王莲珍要给他下跪是何道理。
因为李祥如的儿子李茂离家出走,无影无踪地找不到了,本该在门前单膝跪地恭迎奔丧来客的孝子贤孙只能由内侄、内侄孙来替。
他们的父亲都去车站接白攸了,没成想这城里来的少爷自己租了一辆车就叫人送过来了。此时他们见姑妈王莲珍要跪,慌忙就拦了过来将人劝了回去。
白攸松开手,茫然地望着眼前这一堆乱哄哄的人,不免想起白父与白母的葬礼是那么地冷清。
神父说,自.杀的人是上不了天堂的。
那爸爸、妈妈,现在又在哪里呢?
哀乐再起,白攸的耳边又是好一阵锣鼓喧天、唢呐齐鸣。
吵得他心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