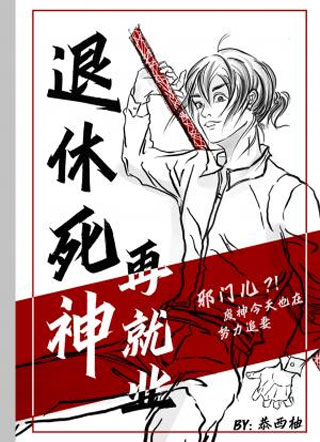
时间:2022-06-12 来源:长佩 分类:现代 作者:恭西柚 主角:月不开 阴沨
月不开原本以为阴大人只愿意和自己脑电波交流呢!哪知道兆琼之也有这个本事,“怎么还有中途加塞儿进群的?”
其实自从见到兆琼之,沨月二人没短了探查她,相互对过几次眼神,都确信这姑娘是“民及民以上”的身份。
再者,在场众人都以为阴沨叫“阴云沨”,陈三爷称他为“小友”,唯独兆琼之跟月不开统一口径,也称呼他为“阴大人”。她这是明示。
阴沨传话:“你有意见?”
“不敢有,”月不开嘴里发酸。阴大人是他用“酒水自由”勾过来的,肯陪他穿一身红走一趟鸿门宴已经很赏脸了。
“疯了吧!斗酒?!这不明摆……”柒陆叁从椅子里弹起来,只是刑巴一米九的身板宽肩窄腰挡在面前,一副逼宫的眼神。柒陆叁叹了口气,颓然坐回圈椅里,嘴里嘟囔:“敢情这椅子成半永久坐骑了。”
小柒爷心说话:斗酒明摆着欺负人!开爷的酒量还赶不上我呢!自打我记事起就没见过陈三爷喝醉过!我老爹也算是海量,遇到陈三爷也要喝趴下的,开爷拿什么跟人家斗啊!
他目光越过刑巴头顶打量阴沨,更加丧气:不成不成!姓阴的最多二十岁,一看就是学生样儿,喝一杯都算多了!约么是个“一瓶盖倒”!
想到这些柒陆叁顶住刑巴的施压,拍扶手再次起身,拽大黄蜂卫衣的下摆,摆弄自己并不存在的架子,难得硬气一回:“斗酒就有点儿欺负人了,你们要真敢这么斗,我跟开爷一队。”
陈三爷摇头发笑,“琼之,另换题目罢。论酒,确实为难他们。”
“不为难,”阴沨说,“陈三爷,院里现在房上房下一共57号人,不如大家一起喝。”
陈永渠一愣,没听明白他什么意思。不仅他如此,就连岿然不动的刑巴也是微微侧头。
“大家一起喝,沾点儿玖珑姑娘的喜气。怎么?陈三爷出不起酒钱?”阴沨说话一点都不客气,面色比地上霜都冷三分。
兆琼之拽了月不开一把,小声问:“他没病吧?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托大?”
“嘶!说什么呢?大腊月光脚踩地,你才小心得病!”月不开暗中怼回去,“阴大人做事有分,比我靠谱。”
“今天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能喝酒的都留下,开车的、不能喝的走好不送,”阴沨声音不高但字字分明,没谁再装听不懂。
这是要动真格的了!
一圈武生大眼瞪小眼,打架以一当十的人大有人在,舌战群儒也有历史典故,但论喝酒,以二敌一院子四五十人?开什么玩笑!
有的人心里犯嘀咕,觉得气氛不对,想开溜又不敢溜,斜眼看陈三爷的脸色。陈三爷无动于衷。
有的人则满不在乎,这事儿多新鲜!说的粗一点就好比小刀捅屁股——开眼呐!院子里人头能凑出两个排的编制,他们一人一杯,保准把姓阴的喝趴下。
“这就是你说的靠谱?”兆琼之哼了一声。
月不开心里也发毛,传话给阴沨:见好就收,阴大人,我真没那么大量……要不咱们使阴招?回吧!回家您想喝什么随便买,不差几瓶酒钱……
差。阴沨只回给他一个字。
得!阴大人就是一醪糟莲蓬,心眼不少,但一孔一眼里全是一汪一汪的老窖糟烧二锅头、茅台汾酒五粮液。
“疯了吧这!一定是疯了!开爷你也不管管……”小柒爷被阴沨瞟了一眼,这一眼让他想起来自己当年考五门挂三科时,他爹老柒爷几乎杀人的气场。
他摸着椅子边坐回去,心想真是邪门儿了,平时他好歹是被尊称一声“爷”的,怎么今晚上愣是没说过一句完整话?没爹罩着,卑微啊……
陈三爷是骑虎难下,话都让阴沨说尽了,可阴沨偏不管那些,只喊:“上酒!”
此一声如乾之动、如雷之发,四座寂然,连树上的乌鸦也不敢多叫半个音节。
陈三爷点头,手下人备上了,清一色的烧刀子老白干,度数上乘,没有小于48度的。除去不能喝酒的和不敢斗酒的,在场还剩31人,陈三爷也是大方,一人一瓶大曲傍一只龙泉青瓷盅。
那股子酒曲香气随着开瓶声弥散开去,馥郁醇厚的酒气犹如无形之雾将览月阁围了个水泄不通,似乎只要多嗅几口就已经足够醉倒人了。
兆琼之下意识去捂鼻子,陈三爷要的都是酱香型白酒,生怕不够味儿似的。兆琼之应付不来这股味道,不用入口,闻多了便发晕,“有钱烧的!真不知道这些辣嗓子的东西有什么好喝的?不如喝可乐冰红茶。”
“英雄所见略同呐!”月不开咂嘴。阴沨把兆琼之的那份酒盅端到自己的托盘里,随后端起月不开的酒盅问:“你要不要,不要给我。”
“要!当然要!”月不开从阴沨手中夺回自己的酒盅,迅速在阴沨的酒盅边缘碰了一下,仰头一饮而尽。
阴沨端杯子冲月不开点点头,并不多说什么,也一口闷了。不必开口,都在酒里了。
紧接着他又闷了两盅,月不开陪了他两盅。在场众人看傻了,陈三爷手中的酒杯端在半空,举也不是、放也不是。
他是长辈,本来打算在大家举杯前说两句套话,谁知道对面二位竟然一声不吭地喝起来了!推杯换盏,有来有往的,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
正当他清嗓子准备说两句,阴沨先发制人:“酒盅太小不方便,您这有酒斗吗?”
现代人已经不用那些老派的酒器了,阴沨有些惋惜,“那我对瓶喝了。”
说着他从身边一名武生手里顺走一瓶“白云楼”,猛灌了一大口。众人这才发现他自己那瓶早已喝空了!
柒陆叁以为酒中掺水了,自己也倒了一满盅惯进嘴里,随后一口醇香口灿莲花一般喷了出去。刑巴侧身躲闪,可酒水还是溅在他过于突出的胸肌上。
“我去!真酒!阴兄弟怎么跟喝水似的,这还是人么……”小柒爷怀疑人生。
这一来,满园子的人无人再敢下口了,不仅不敢喝,甚至连抬眼看阴沨的勇气都没有,生怕和他对上眼,万一被这位“酒腻子”敬上一盅,恐怕要喝到胃出血。本就是薄雪过后天寒地冻的时节,有阴沨在,凉气更是从脚底板往身体里钻。
院子里静得怕人,阴沨脸白,一身玉红长衫罩在他身上瞧不出半分喜庆,只衬得脸色更加惨白,像白纸扎花似的,在不大的院里飘。好端端一台喜宴愣是笼罩了一层阴曹地府的感觉。
他拎着酒瓶子绕圈,眼中没什么神色,只是遇一人灌自己一口。一个被他找上的武生哆嗦起来,洒出去半盅的酒。阴沨当即逮住他的手腕子,“端稳一点。你怕什么?我只喝酒,不吃人。”
那短打武生精气神全无,他感觉到阴沨的手极冷——哪里是手,分明是森森的白骨爪子!小指上的一圈玉指环渗血一般的红,像是刚刚喂饱了血的兵器。
这气氛不对劲……太不对劲了!
“阴沨,阴大人,你是不是不开心……”月不开试探着在心里问。阴沨没有回答。
看来他确实心里有事。
月不开提酒跟上去,按照阴沨走过的顺序遇一人敬一盅。院中小辈都被阴沨吓傻了,月不开嘻嘻哈哈打圆场,试图把冷到冰窖的气氛炒起来——
“我跟您们说,这位阴云沨啊,别人叫他阴爷、沨爷他保准不乐意,只能叫一声‘大人’!
“什么?您没听说过阴大人?那您听说过包大人吧?一个意思!这人能耐大、脾气大,脸够冷来是心够硬,这才称上大人!”
月不开抹开脸,自己一个人自逗自捧,单口相声似的。兆琼之在一旁扶额,他那一身大褂卖弄起来还真有几分流氓艺术的风范。“那是,我还会拉二胡呢,老人民艺术家了。”
几盅酒下肚,他脸就红了,嘴上滔滔,口齿清晰得很。他挑了一个倒霉蛋拉着人家絮叨:“您别看他姓阴,这姓氏少见吧?其实他也姓陈,和您家陈三爷同祖同宗呢!”月不开胡侃。
“有朋友就要问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姓阴和姓陈这不差了十万八千里么?赶上去月球的距离了!我跟您们说,”月不开故意压低声音,“他姓陈,名叫陈年水龙头——真的锈(秀)啊!”
周围几人想笑又不敢笑,咧嘴的模样比哭都难看。
“嗐!抖个包袱没把大家逗乐,怎么反倒哭起来了!我自罚一杯!”月不开又端了一杯,酒入口就像刀子似的从喉咙一路剐到胃口,他脚下一没留神差点连人带酒栽在青石板上。
须臾恍惚之间,只见得幢幢灯影随风明灭错落,那人一身红衣似喜服、似浸血的战袍,一样的绝艳、一样的触目惊心……
他是死神呐……不死怎入地府?
不死,何以成神?
经年往事和眼前的场面重叠在一处,月不开甩头强迫自己清醒一点。“不要总记挂从前的事,阴沨忘了,忘了才好,”他想。阴沨是穿过红衣的,只可惜他留给自己的永远是一个背影。月不开希望他现在可以回头看一眼。
可阴沨从不回头,从前如此,现在……亦然。
“琼花房,金盘露,
览月阁前雾。
一纸残谱功名箓,
汉泉遮天幕。
白云楼,白发囚,
不似泸州月色稠。
挂刀何堪断水流,
此去无筹、无仇、亦无愁!”
阴沨提酒行诗,嗓音温煦而暗藏锋芒,在院中走上一圈之后站定中央位置,身轻气清,无丝毫醉态。
“好啊!好一个《喜迁莺》,”陈三爷瘫软在靠椅里,对面大戏楼“览月阁”的大匾在他眼中重出五重影,他缓缓拍掌,口齿模糊:“沽酒钓月,当真……当真风雅……”
兆琼之暗暗称奇,之前她能夸一句“阴大人酒量逆天”,现在却什么都夸不出来,只能用“不明觉厉”四字来代替。但她隐约察觉出一点不对劲——脚底下的青砖地面竟然是温热的,而且越来越热!
兆琼之的鞋早就踢给小柒爷了,所以比那些穿千层底的武生感觉更灵敏一些,她悄声问月不开:“到底怎么回事?你又搞什么鬼!”
“听听,听听您说的什么话?什么叫我又?”月不开不满地哼道。他也发觉温度不对劲,哪有越到半夜越暖和的道理啊!
他回想起方才阴沨在院中走过的路线,再加上他最后站定的位置,瞬间酒意全无!
“我操!阴沨你想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