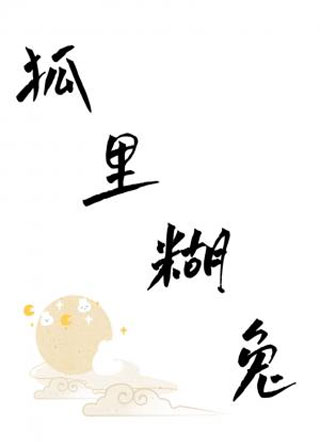
时间:2022-02-15 来源:长佩 分类:现代 作者:奉壹 主角:狐狸 白兔
大年初一清早,白兔还没睁开眼就被狐狸叼着后颈皮走了一路,最后呱唧一屁股摔在灶王爷的朱木大门前。
它还梦着在太阳底下烤得脖子暖烘烘湿乎乎,立时痛到大惊转醒,两颗兔板牙刷地呲出来:“哪个挨千刀的王八犊子——啊哟!”
“说吉利话。”狐狸从他白唧唧软嘟嘟的屁股上收回犬牙,蹲坐着噗噗吐了几根兔毛,又伸手将它两只长耳朵往上一提,“好好拜年。”
白兔被拎直了抻开,从头到尾活像根胖白萝卜,粉鼻头一鼓一收,敢怒不敢言:“毛尽给你薅光了!”
那狐狸斯斯文文坐得板正,阖眼兀自不答话,过了一会,瞥瞥脚旁蓬乱的白团子,又俯身仔细把它舔得皮亮毛顺,舒服得几根胡须直颤。
昨日人间小年,灶王爷乘风下凡享贡,天南海北走了一圈,见自己声望如春竹年年拔节,兴得意满,自是饮酒作乐一番,起得相当晚。
等到扎双髻的小童前来迎客,白兔已困得云里雾里,被狐狸摇将醒,连人都不看,张开三瓣嘴,破锅里炒豆子似的,颠来倒去重复“万事顺意,年年高升,福如东海”。
可怜它兔脑袋本就容量小,又馋又懒,狐狸教那么多,他筛了又筛,统共就记得这么两三句。
小童碍着狐仙在场,没敢笑出声来,行礼时肩膀抖了三抖,转头引路。
天宫里其他神仙都好花喜草,品味高雅,唯独灶王爷园子里种的尽是四时果蔬,鲁葱淮枳,风一吹,满园植物荤素气。
三拐两绕进回廊,狐狸一低头,忽然发现白兔不见了。
他淡金的眉跳了两跳,立刻原路返回,发现白兔正勉力将两只板牙嵌在菜圃中有他十倍大的南瓜里,两腮鼓鼓,咔嚓咔嚓吃得津津有味。
狐狸将灿火似的大尾一摆,轻哂一声,有些无奈地过去又将他叼了往背上一甩,任由他又蹬又抓也不放,这才相安无事入了大殿。
马马虎虎同灶王爷拜过年,白兔心不在焉地抽抽鼻子,循味见一旁桃红木小几上盛着一碟新做的凤梨酥,顿时满嘴潮湿,蹲着挪了挪屁股,跃跃欲试地要蹦上去偷吃。
狐狸正同灶王爷聊着近来天上凡间种种琐碎,余光瞥见,随手抓了两块,弯腰递到他面前。
白兔还生着闷气,瞧也不瞧他,拿嘴从他手心叼了一块,又伸手抱走一块,转头一溜烟冲出殿门,找了个草垛子窝起来吃甜点心。
没睡饱的缘故,吃着吃着,又犯了困。
隐隐的,山那头有清凉远风吹过来,一并把屋里的话声捎带上了:
“狐仙,实在糊涂呀。几百年了,你同他这段孽缘……”
白兔正团卧在一株黄姜花下,被小虫透明的翅翼搔过鼻尖,一拱头打了个喷嚏,浑身白毛蓬炸起来,半晌才恢复原样。
午后,狐仙殿里燃着白竹香,堂中仙乐绕梁,循声望去,几只小狐正用后爪立在木凳上,挥汗如雨地弹琴击鼓。
几步开外,白兔躺在红木仙人椅上四爪摊开,朝天翻肚皮,睡得兔事不知。
一曲还未完,门帘突然一掀,狐狸裹着股寒气走进来。他进门便化作人形,一身玄色披风上落了许多细雪,摆一摆手,几只小狐四爪着地,悄没声儿地溜了。
殿里转瞬只剩一狐一兔,静到能听见炉里木柴烧得噼啪作响。
狐狸踱到椅前,垂目注视着毫无知觉的兔子,火红竖瞳逐渐扩成柔和的圆。
好半晌,等暖过来了,他才用手背小心地在那雪白绒毛上轻轻一捋,比春风还缓。
那白兔梦中却有感觉,一翻翻个儿,手脚并用锁了他修长的手掌,迷瞪瞪骂:“臭狐狸,趁我睡着偷溜,我非咬掉你一块肉不可!”
说完,当真恶狠狠落牙去咬他。
那狐狸既不辩解也不恼,反而伸出一根手指从他兔脑袋慢慢摸下去,直把白兔摸得软似春水,张着嘴发痴,什么深仇大恨全忘光了。
“今日雪急。”半晌,他才温声宽慰,“你喜欢的那片仙蓿草遇潮,翻过山去才找到几株。”
白兔咦了声,迟钝地趴起来,用一双红眼睛盯他:“你,你是为了去摘那草……”
才淋得浑身这样湿透?
狐狸却不欲再谈下去,“今晚宫里有夜宴,你不用等我,早点休息。”
“谁的宴?”
狐狸顿了顿,如实道:“虎王新得一子,叫人去吃满月酒。”
“哼!”白兔冷不丁愤懑起来,“向来如此,有用的儿子便大办酒席,没用的恨不得立刻一脚踹出来,任人亵玩侮辱!”
天宫的仙兔们大多满月便能习字学诗,可唯独他半岁了还不能开口说话,灵识未醒,一断奶便被当作野兔子胡乱裹着绸布扔在路边,白给这狐狸捡去。
出了火方才想起自己这话有些伤人,待抬眼去看,狐狸依然是满脸平静,眼角眉梢不明不白含着点笑意:“没必要置气。”
白兔哼了一声,却没和他争嘴。
说到底,要不是臭狐狸日以夜继助他化透灵识,又拿各种仙丹灵草给他筑基,只怕他现在困在一团混沌里。
白兔懒洋洋地趴下来,把两条长后腿踩在他掌心,定定地发了会儿呆,才说:“我也去。”
“……”狐狸捏了捏他粉嫩嫩的爪子,不正面拒绝,兀自盯着他瞧,“若是再溺了……”
“那回是饮了太多酒!”白兔猛地蹦起来尖叫,内耳脉络红得和眼睛差不了几分,“区区几只狮子老虎,本兔还不放眼里!”
屋角燃的白竹香屑在弯脚红泥小坛中簌簌落了一捧,只听狐狸低声闷笑:“随你。”
入夜自是一番梳洗打扮,舐毛净爪,白乎乎往狐狸脖子上一圈,成了条上好的兔围脖。
天界宴会大多把吃荤的和吃素的分两边儿,狐仙食素的名声在外,位置倒成了楚河汉界,左边挨着只吃鱼虾的河马大仙,右边则是鹿仙。
仙既修成了仙,便不受世情俗欲欲所控,偶尔吃些东西也仅为过过嘴瘾。狐仙连筷子都不拾,只拿白玉似的修长手指捏着酒杯把玩。
玉壶中的桃花酿是拿天泉水洗濯泡过的,甘凉清甜,香气浓郁,真真仅这天上独有。
白兔馋得要死要活,伸爪欲偷,给狐狸一根手指拨得东倒西歪。
不等他喷火,狐狸先拿指尖沾了一滴喂到他三瓣嘴里去。
酒一入口,白兔立刻抱着他手指飘飘欲仙地吮,拿小舌依依不舍地卷着狐狸指尖,回味无穷。
只见那狐狸两只尖耳扑簌簌一抖,面上强自镇定,蓬尾却已在坐垫上摆起了微风。
这当口,望不见尽头的流水席前方突然一阵鼓响炮鸣,是各宫王仙给虎王呈礼送宝的时候了。
狐仙嘱咐了白兔两句,抽身而起,跟在河马大仙后面往前去。
那白兔目送着狐狸走没影儿了,立时蹦起来去捣弄酒壶,未想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嗤笑。
白兔扭头去看,是只脖上挂着翡翠细珠链的灰兔,仰着下巴颏,正蹲在小台上睨他。
白兔很不客气:“你看什么看?”
“我嘛,”灰兔滴溜溜一滚眼珠,“头回见到天宫里的兔子献媚卖皮,自然好奇。”
“放你的兔子屁!”白兔大发雷霆,两只耳朵直挺挺地抖抖抖,“我对臭狐狸?他也配!”
“配不配的,我们都瞧在眼里。”灰兔冷笑,“你自个舒坦就成,反正早被踢出了族门,丢的也不是我们的脸。”
白兔何时受过这种气,恨不能一蹦三尺高,龇牙咧嘴:“我当然舒坦!我在狐宫吃香喝辣,花狐狸的用狐狸的,自然要比你个无名小卒过得舒坦!”
他说的可真是实话。在狐狸那儿,他生活得要比兔宫许多兔子还舒服,平日里饮之仙露,饲以茗草,谁的脸色都不必看,更别提那些奇珍异宝,探宝镜,玲珑环,千层杯,他闲时嘟囔两句,狐狸听了,虽不说什么,可过两日便给他搜罗来。
那灰兔脸色一扭,不屑地一抬下巴,讥讽:“果然是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蠢材!谁不知狐仙早对我们兔仙大人爱慕有加,他救你,助你化形,不过是把你当做——”
“阿勉!你越发不懂事了。”
那灰兔还要说下去,旁边突然传来温淡的一声喝止,语气虽不严厉,却让它立时闭了嘴。
白兔还未抬头,只闻一阵桂花清香,绣金线刺银珠的袍脚在眼前簌簌而过,千树万树梨花碎金,恍得几乎忘了身在何处。
唤作阿勉的灰兔算是得了靠山,喜得大叫:“兔仙大人!”
当年白兔被踢出族门时没有任何记忆,还是通了灵识后才知道此前种种。如今一看兔仙,果真矜贵非常,可也就是这个兔仙,心狠手辣地将自己驱逐了!
两个敌人!
狐仙恰好和兔仙前脚后脚回来,看了一眼满脸愤懑、胡须炸起的白兔,微微蹙眉,“怎么回事?”
“族里的孩子不懂事,扰了狐仙大人清静。”兔仙歉疚地将灰兔抱起,轻轻一低头,“还望大人不要计较。”
“兔仙多虑了。”狐狸也彬彬有礼地颔首。
灰兔被抱在怀里,趁机使劲冲白兔挤眉弄眼,那意思分明是说:你瞧好吧!
白兔方才记起他未说完的半句话,半信半疑仰头去看,那臭狐狸果然都不像臭狐狸了,一把紫竹折扇捏在手里几乎要玩出花来,眼角眉梢含笑,只定定地望着兔仙。
爱慕有加?是真的?
救他,助他化形,难道就为了把他当作兔仙的影子?
想着想着,胸口一痛,白兔感觉心底灼灼的简直像要烧起来,顿时鼻尖发酸,恨得咬牙切齿——这狐狸岂敢,他岂敢!
他承认他对狐狸的确不及狐狸对自己半分好,但却从没做过有愧于狐狸的事!
这些年来,他愿意和一口就能把他整个儿吞掉的狐狸睡一张床,愿意和他朝夕相对,愿意心情好时帮狐狸舔舔毛,是因为他以为狐狸抱了和他同样的心思,不是因为他把狐狸当做谁的替代!
怒气中没听清两个仙又说了什么,身子一腾空,这才发现原来已经被狐狸揽在了肩头。
白兔勃然大怒,立时挥了一记兔拳打在狐狸下巴,又嫉又妒地扒着他肩头往回看,只见那兔仙也正遥遥望向这边,目光中几分悲悯,几分叹息,随着清风明月,渐渐远了淡了。
“呼嘿!”
白兔左右摇摆着肥嘟嘟的屁股,全力往前一蹦。
草叶蓊郁,被他扑得乱摇,塌了一块下去。原本停在那里的小青蛙早不知道去哪儿了,空啃一嘴泥。
白兔恼火地爬起来,呸呸呸一阵吐,发现旁边几只小狐狸吱吱吱笑成一团,顿时懊丧地往地上一躺:“不玩了不玩了!这怎么抓得着!”
其中一只三花小狐闻言,细长的耳朵抖了抖,刷地窜出去,不消片刻便叼着那只肚子鼓鼓的青蛙回来了。
白兔龇牙咧嘴:“你真能!”
“这算什么呀,”三花小狐傻憨憨的没听出讽刺,说,“大人比我们厉害多了!”
“他?”白兔更加冷嗤,“他就是个臭狐狸!”
那日夜宴归来,从他在狐狸榻上撒了一泡颜色金黄的兔尿开始,他已经赌气冷了狐狸一月多。
这一个月他日日和小狐厮混在一起,那狐狸非但不生气,还专点了几只小狐,日夜陪他胡作非为。
渐渐地,连冬末都过完了,天宫里已是漫山遍野的春绿,草木泛香。
小狐到底不高兴他贬低自己大人,沉不住气地扁一扁嘴,“本来就是嘛!只不过大人他成了仙无需食五谷,我们还要捕食而已。”
“冲他说这有什么用?”另一只绿眼狐狸凉哂道,“大人上回被黑熊抓的伤至今未愈,最近还总是饮酒。”
“这么一说,”小狐狸抹了抹嘴,又去舔爪子,“大人最近的确郁郁寡欢的。”
白兔茫然地趴起来,“你们说什么呢?什么黑熊?”
“小主的心可真大。”绿眼小狐翻了翻眼珠子,“你都忘记自己明里暗里地讨那百物囊啦?”
白兔一下子傻了。
他不过是看话本里说那能装纳天地的奇物,心痒痒地给狐狸讲了一次……
那臭狐狸,怎么什么都做真?敢去和黑熊抢东西,是不要命了吗?
等等,臭狐狸就算受伤又关他什么事,反正也不是真心想把宝物给他吧?只是看在,看在他与兔仙多少有点相像的份上。
竭力给自己找着理,几只小狐突然同时扭头,警惕地朝上风处看去。
草叶依然在熏风中沙沙作响,有几只花蝴蝶轻飘飘地飞起,又点落。
绿眼小狐猛地扭过头,对白兔大叫:“快跑!”
他的眼珠紧缩成了一条细细的瞳,吓得白兔猛然跳起来。
他突觉这些平时任他指挥的小狐一个个都这么高大,有力的后腿蜷着,两腮发厚,尖牙利齿。
与此同时,方才风平浪静的绿浪之中刷地跃起一只黄皮子,尖牙利爪朝他扑来,几只小狐喉咙里发出低吼声,齐齐跳起阻拦。
两方纠战在一处,用的全是牙齿和爪子,次次朝最要命的脖子和心窝招呼。一时草屑翻扑,肉食动物你死我活的狠厉瞬间展露无遗。
白兔到底是只还未能化人形的兔子,什么时候见过这等场面,惊吓到呼吸停止,头晕眼花了好一会儿才跌跌撞撞转身,不分东南西北地拼命狂奔起来。
那黄皮子也精得很,瞥见香喷喷的肥兔子已经跑了,眼前只剩几只又小又臊气的狐狸,也不多作纠缠,一手掼倒一只小狐,越过它们撒腿便追。
它四肢修长,眨眼便已跑了十几步远,眼看要撵上那抹若隐若现的白色。
绿眼小狐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大急道:“糟了,快去报告大人!”
风吹草低,一望无际的草坡上,一白一黄两个小点正在全速前进。
白兔这辈子没跑过这么快,狂风刮得两只长耳朵尽数往后倒贴在背上,整个身体里像窝着一团火,腾腾地乱烧。
他满脑混沌,仓促中记起那黄皮子长嘴细眼,竟无端想起狐狸来。
狐狸,狐狸对他再好也是只狐狸,而他不过是钝牙无爪、任人揉圆搓扁的掌中之物,谁知道狐狸什么时候也不耐烦养他,本性暴露,也一嘴便将它吞了?
如此这般想着,心里另一个声音却道,要吃早吃了,等你这几百年!遑论他早已成仙,吸纳日月精华便足够。
但转念又一想,故事里不也有神仙拿至纯之物供养着生灵,最后炼化了拿来补精气?
他越想越远,忽然感觉屁股蛋上一阵热乎乎的哈气,扭头一看,黄皮子咧着涎水牙,眼看要咬住他短蓬的尾巴——
白兔肝胆俱裂。
突然,前方的草叶无风自转起来,先是一道模糊的火红的影,随后颀长身型渐渐显了真身,只见那人穿一身青色竹云束腰袍,桃花眼尾向上轻挑,大尾灿如金火,还未立定,修长如玉的手已向白兔伸来。
“狐狸!”
白兔大叫,一跃而起,顺着他胳膊急急往上爬。
此时也顾不得什么恨什么怨了,白兔紧团在狐狸颈窝处,整个毛绒绒的兔头全扎进了他领口,浑身抖若筛糠,是个鸵鸟的姿势。
他狠嗅狐狸袍子上熟悉的熏香,满脑子只想着,你怎么来得这样晚!
“黄小仙。你好兴致,”狐仙抬起一只手安抚他,冷冷开口道,“今日还没入夜便藏不住了么。”
话音未落,只闻一阵尖细狂笑,那黄皮子摇身一变,化作了人形。
是个个子很高的男人,但尾巴干枯,四肢细长,瘦得简直有些尖嘴猴腮相,鼻尖眼底都是黄色,不是狐仙那种明丽流转的金瞳,而是深腻的沉淀色,像放久的油。
“原来早被狐仙大人发现了!嘻嘻,可真新鲜真有趣哪,”他斑点密布的鼻子痉挛般抽搐几下,“我竟不知狐仙大人就将这兔子养在了自家后院。这样日夜不离地见他,不是平白受剜心之痛?”
“或许吧。”狐狸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比不得被流放的丧家之犬。”
“狐鼠本是同根生!”黄小仙眼中凶光爆射,“我兄长已去,天道有轮回,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轮到你们了!”
说时迟那时快,一道尖锐厉光从他指尖闪过,纵然狐狸飞快闪躲,可风里仍飘散开几根被削下的火红狐毛。
再回头去看,黄小仙早已不见踪影。
几只小狐没有遁身之术,方才气喘吁吁地从大殿赶来,见这一幕,顿时着急地立起叫唤:“大人,不追了吗?”
“罢了。”狐狸眯了眯眼,修长手掌托牢胸口那一小团瑟瑟发抖的温热,“今夜他若敢再来……”
仿佛怕吓了谁似的,熏风中,后半句话音渐渐消弭了。
等回到狐殿,白兔从狐狸袍子里稀里糊涂滚出来,好半晌才从惊厥中恢复一些,又是吓又是累,整个兔一下子蔫了,撅着屁股趴在冰珠席上,许久也不动一下。
可偏偏有只狐许久没近过他身,好不容易逮到了机会,怎么也不肯让他安歇。
一会给他放小冰鉴,一会点安神香,一会给他梳毛,一会又靠近打着扇子絮絮细语:“今日西弦山脚下长出的铃菇,一半拿去给你放了菜汁炸酥,另一半做椰蓉甜饼,可好?”
铃菇是相当珍贵的食材,整年只出一次,错过了便要再等下一年,白兔耳朵一动,目光灼灼地转头,迟钝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自己正和臭狐狸冷战,顿时气急败坏地用力捶软枕:“不吃不吃!减肥!”
一捶才发现这只软枕还是狐狸专门给他缝的,比平常枕头小得多,圆圆一只,走线严密,面儿是天蚕绸,里子则用二月小鹅的护心毛,右下角还勾勒了一只小兔的形状,已经被他睡出了几根线头。
见他发呆,狐狸支颔轻笑,温声道:“不是说这铃菇最养皮毛?”
噢噢,所以也觉得他胖了,是吧?
那还缠着他作什么,有这功夫,不如拿去冲高贵的兔仙谄媚好了!
白兔一骨碌爬起来,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几根长须乱抖:“你再怎么给我吃这些仙草也没用的,我全不成气候!到现在都化不成人形,既没出息也没本事,死也成不了你喜欢的兔仙!”
他喊着,浑身毛全炸开,活像只白刺猬,但一团水光在眼里转啊转,倔强地怎么也不肯掉下来。
狐狸看得心疼,微微蹙眉,刚伸出手要碰一碰他耳朵,白兔却猛地往旁边一窜,在他掌下划过一道茸茸白光,跑出去很远了。
手指还停留在虚空中,半晌,狐狸涩然一笑,把失落的掌心攥紧,尾巴甩一甩,也无精打采地垂下来。
子夜如墨,凉风里桂香浮动。
狐殿书房内,狐仙正对着一挂卷轴饮酒。
房里没点烛火,全凭玉色一般的月光照明,只见卷轴上画的人风姿绰约,正在低头逗弄怀中一只小兔,腰间的翡色荷花玉佩上雕刻着兔仙二字。
这画显然是趁人不注意偷偷作成,笔触稚嫩,然而眼角眉梢都十分灵动,显然是被珍而重之用心描摹过的,作画人不知仔细观察了多少次。
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天宫中人人都说,白兔是他捡来的家族弃子,连白兔也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是他披风戴月,在帝皇殿前苦求了几百个日夜才向天帝求来的机遇。
但是他什么都不能说,只有静默地等待那一天来临。
几百年间道不破的天机,是他甘之如饴的枷锁。
好在,那一天也快来了。眼下他已经能嗅到桂花暗香,窗外促织蛩声细细,檐角的月也盈满一圆,与几百年前没什么不同。
无论天上人间,年年岁岁月色相似,人却早不是同一茬了。
狐仙慢慢合上画轴,拎起酒壶饮尽最后一口,薄刃划喉。
白兔团在软榻上睡得正香,忽然察觉身侧一陷,随后一只手在他耳后轻轻摸了摸,又顺着背脊捋下去。
正是骨懒筋酥的时候,白兔嘤咛一声,毫无戒心地翻出软软的肚皮给来人摸。
只听得那人轻笑一声,如千树万树花瓣被一阵清风悠悠吹落,白兔猛然转醒,水亮亮眸子里倒映的不是狐狸又是谁。
笑,还在笑,这是当自己像只狗似的讨他欢心了!
白兔恼火地翻身而起,却又被他适时拢住尾巴一捏,顿时从屁股麻到耳朵,呜呜叫着一下子趴了回去,眼角都沁出泪来。
尾巴,尾巴,命根子尾巴!臭狐狸明知他那尾巴是最碰不得的!
白兔凶恶地瞪着泪眼去看狐狸,却发现对方一手控着他,一手支着下颔,长睫半垂掩着金光,满头鸦发未盘,一副疏懒疲乏的样子。
“还不松开!”
白兔大叫,用力想要逃身,却被狐狸轻松一手翻了个面儿,头晕目眩,半晌没缓过劲儿来,睁眼便看到狐狸两枚犬牙在唇下微微冒着尖,寒光凛凛。
白兔惊惧交加,夹着尾巴瑟瑟发抖,身上一阵热一阵冷,两行泪水直直渗入纯白的毛里:“你吃了我算了!”
那狐狸本来小心翼翼地将他搂抱在肩头,像捧着什么宝贝,猛然间被这话扎得浑身一抖,如遭雷殛。
低头看到白兔紧闭双眼,视死如归的模样,他默了半晌,终于身影一摇化作原形,用蓬茸大尾将白兔裹在怀里,伸出舌头细细给他舔去那两行湿泪。
刚刚一通折腾,白兔身上的毛也一绺绺乱着,狐狸渐渐不自觉地往下舔,舌尖扫过心口的细毛,柔软的肚腹,渐渐把白兔舔得身体僵直,鼻梁发抖,整只兔像要化了似的,偏偏又被狐尾缠得动弹不得。
那湿热的舌头舔到两条后腿中间时,白兔终于难以遏制地挣出爪子狠狠扇在狐狸脸上,啪一下扇得他朝左侧脸,又啪一下向右。
“滚开!”他羞愤欲死,脚也上阵蹬他,“全是酒味,臭死了!”
这狐狸吃醉了酒怎么这么缠人!
白兔到底没伸出指甲来,打的是软绵绵的蜜巴掌,狐狸却恍然惊醒,拉开距离,有些受伤的样子,呼吸压得清浅,只拿一双深邃含柔的眼睛默默凝着他。
桎梏的狐尾已经松开,可白兔被他那样望着,全然忘了逃脱。
这到底是他看了几百年的狐狸。多少个四季轮转,从有灵识有记忆起他就在他怀里打滚,被那朱金赤瞳望着,被那长尾一摇一摇逗着满床乱蹦。
窗外忽然一阵风动影移,遥遥飘来清甜的桂花暗香。那双金瞳随之眨了一眨,好似浮着一层浅亮的水光,半晌,狐狸撑不住似的略略一歪身子,薄唇轻动,低声唤他:“兔仙。”
白兔怔怔地望着他,眼泪却先一步滚了下来。
错了,全错了,原来这泪竟是他眼里的。
三更时宿醉转醒,狐狸倦怠地睁开眼睛,忽然见屋中堆着高高一摞宝物,白兔手脚并用,还在吃力地扯一只粉彩蟠桃大宝镜。
狐狸有些疏懒,单手支起下颔,声音低哑:“入了夜还不睡觉,这是做什么?”
白兔并不看他,依然哼哧哼哧地挪东西,“还你你的东西!咱们两清!”
闻言,狐狸忽然翻身而起,走过去将银镜拿在手里掂了掂,却是往原处一抛,面上怔然,眼底抑制不住流出几分苦楚神色:“还完这些东西,就算两清了吗?”
“算不清,是算不清。”兔子咬牙道,“我知道我欠你的多了,但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要杀要剐,任君喜欢!”
狐狸沉默片刻,忽然淡淡一哂:“我拿自己的命赔给你都还嫌不够,要你的命作什么?”
说完,他转身出了殿门。白兔立在原地,听他低声和门口的小狐嘱咐了几句什么,随后脚步远去,再无声音。
白兔抖了抖耳朵,颓唐地瘫坐在地,把狐狸那话在脑袋里反复琢磨,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发了许久的呆,白兔忽然一瞥,发现那狐狸将丛竹暗纹外袍落在了床边。
他一步一蹭地蹦过去,伸着头往宽大袖筒里一钻,只闻扑鼻的白檀清香,夹杂几分桃酿酒气。
他终究有些贪恋,恹恹地钻进去,心想,他还不如狐狸一只袖筒大。
为什么,为什么他就是变不成人啊。
白兔动了动,把头紧埋在两只一丝杂毛都无的前爪里,不一会,那毛竟渐渐濡湿了。
几日后,夜。
吧嗒吧嗒,狐爪磕地作响,只见两只小狐狸费力地抬着一大木桶热水从狐殿门外走进来,月亮将它们的影子拉得细长。
走到中庭,那只矮小些的狐狸忽然把耳朵一立,不着调地嘻嘻笑道:“师兄师兄,他日我若长成这般身形,定能生出九根红尾巴!”
另一只小狐沉稳地把桶抬高,不着痕迹地将重量多匀些到自己手上,嘴上却毫不客气:“骚包!”
两只小狐身后,月影如流水般淌过殿内亭台楼宇,一并淌过小阁内下了一半的棋局。
那是白兔和狐仙初春时对弈的残局了,狐仙不说收拾,没人敢挪它一丝一毫。
时日已久,也是奇怪,棋盘方格间虽积了些细小的落花残叶,却不见一丝灰尘,连一枚枚黑白棋子都是圆润锃亮的,简直像……有人日日专门来拭净一样。
一大桶热水直接抬到了白兔的偏殿,这些日子狐狸嘱咐要给白兔每夜药浴,白兔任凭他去折腾,每每冷脸相待。
这药浴用的水从一大早就开始煮,里面的山参、乌头、活露、鹤骨等等珍稀药材,熬成稀少的一盆精汁,白兔每次泡过之后总感觉五脏六腑又热又痒,每一日都要比前一日更剧烈些。
这晚他泡过后,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肚子里火烧火燎,忍不住拿爪子挠床,拿头乱蹭,拿钝钝的兔板牙使劲儿咬小枕头发泄,总感觉浑身骨头都生生地泛疼,愈演愈烈。
雕花檀木窗外的玉盘好大一轮,白兔仰着脖子苦苦看了许久,终于一骨碌爬起来向外跑。
他也说不明白为什么要跑,但一跑起来,身上就没有那般疼了。
出了屋门,白兔下意识要去正殿找狐狸,等跑到殿门口却愣了许久,回过神,小声地狠狠骂了句什么,扭头往完全相反的方向往前使劲蹿。
狐殿大门前竖有一道琉璃影壁,底下拿工笔细细描了一排兔子的侧影,那是狐狸每隔一百年便要白兔站在这里画一次的,从小小一团到很精神的成年兔,过往画的那些也被人仔细补过,颜色很新。
白兔路过时停下脚步,在最后一只兔子侧影那里比了一比,果真是完全相同的大小,耳朵,鼻子,胡须都能一一对上。
他呆呆地发了会儿愣,犹豫片刻,还是转过身,四爪着地一路跑出殿门。
殿前挂的红灯笼随风轻摆,将他的影子拉成长长一条。
他心底着实有种隐隐的预感,又惶惑又期待,逼着他不停地向前去。
直至狂奔到那日被黄皮子追赶的草地上,白兔鼻翼快速翕动,再也无力继续前进。
已经入秋,夜风清凉,草坡上遍洒清霜,体内那把旺火却好像要活活烧死他。
白兔呜咽着将自己紧紧蜷缩成一团,两爪牢牢摁住长长的耳朵,整只兔子还不及人的手掌大小。
身后有草木轻响。
狐狸悄无声息出现一棵桂花树下,也不上前,只是远远地望着那一团白,漂亮蓬松的长尾死死绷紧。
幽香白花灼灼纷飞,掩却了他一双幽深眼眸中万千情绪。
白兔根本无心注意这些动静,他几百年来被人捧着宠着,哪儿吃过这样的苦,当下已是痛得瑟瑟发抖,牙根都快要咬碎。
生生忍了半柱香的时间,毫无预兆地,一道白光猛然从他心口爆射而出。
光线刺目,白兔的四肢,脖脚,毛发竟徐徐渐长。
这世上最痛的是什么?五马分尸,凌迟缢首,炮烙腰斩?还是生剥皮,活抽筋,醒拔骨?
那些根本敌不过白兔此时受到的半分,他嘶叫着,七窍汩汩流出浓血,狼狈地满地打滚,哀哀求饶,四爪狠狠抓入身下泥土,指甲尽数崩裂,只恨不能登时就死去。
那喊声先是濒死的兽类,紧接着便成为紧绷的少年音色,最后戛然而止于一声凄厉的寒蝉清鸣。
薄云遮去了月,夜色便如一滴浓墨落在天空,层层化开。
许久之后,白光渐渐消止,远望而去,月色中躺着赤|裸裸一少年郎,眉眼清朗若柳叶新裁,一头乌发似缎,玉面雕琢,正纯真安然地蜷缩在月色之中。
狐狸守了少年一夜。
他拿指尖轻轻描摹少年隽秀漂亮的眉宇,鼻梁,朱唇,反反复复,因为惦念了太久太深,闭上眼也能分毫不差地画出来。
三更时分,露水上来了,不知何处传来羌笛悠悠,狐狸脱掉外袍,仔细裹在少年身上,竖耳静静地听着。
半夜恸曲。
天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狐狸抬眼打量了片刻,突然张口,向半空吐出一枚浑圆金黄的内丹。
只见那内丹上下浮动,金灿灿的,浑圆无暇。狐狸伸出修长的手指,慢慢引着它向下,向下,直至完全融入少年的胸膛。
从头到尾他都太平静了,仿佛那饱含千年灵力的内丹不过泥丸,随用随捏。
旭日完全升了起来,天地间光芒万丈,怀中的少年仿佛也被注入了生机,一双天生微翘的嘴唇很快变得红润,连皮肤都不再苍白,指甲粉亮有光,眉眼灵动,仿佛下一刻便能睁眼坐起来。
狐狸迷恋地看了许久许久,慢慢垂下头,万千青丝顺势滑落到少年面颊。
纤纤光影之中,他克制着轻轻吻过少年温热柔软的嘴唇,惶恐惊醒他一般,不敢用力,蜻蜓点水般落下,又飞快抽离。
他们中间淙淙流过了几百上千年的时间,风云几度变换,他爱他爱至极深,视若珍宝般捧在手心,留在心尖,竟也只在这给他灵力,还他残魂时吻过一次。
或许是怕再留也是眷恋,一吻结束,狐狸轻轻将少年放在柔软的厚草之上,毫无迟疑地飞快抽身,踏着晨光无声无息离开了。
他一路踏风驰云而上,大约半柱香时间,忽见前方九重天庭玉柱及顶,祥云缭绕,一只红嘴仙鹤立在泠清池旁,远见有人登梯而上,长而瘦的腿略一拨动,仰头发出嘹亮的清鸣,振翅飞去。
狐狸于是停住脚步,静静立在阶梯上等着,一身月白色中衣清淡得仿佛要融入云里。
片刻功夫,那只仙鹤归来,将嘴里衔的一枚玉佩嵌入柱石凹槽之中,四面幻境逐一散去,远处高堂中仙乐隐隐,视线所极之处,端坐着这天地间最高贵之人。
“狐仙拜见天帝。”狐狸一撩袍跪下,深深作揖,“小仙前来还誓。”
那人仿佛是叹了口气,声音远得像从天边传来:“狐仙,你的族人要怎么办?”
狐狸半掩着眼,一双赤金瞳仁渐渐被长睫遮去了光芒。
他答:“交予兔仙。”
闻言,天帝连连摇头:“你这是何苦呢。”
“命薄书因果,得失有定数。”狐狸唇畔噙着淡淡苦笑,恭敬万分地向前拱了一拱手,“恶因必结恶果,偷得与他这几百年闲暇,狐仙已再无所冀。”
从前他下凡历练时总听人间的戏文唱沧海桑田,云谲波诡,苍黄翻覆,其实天上也是一样的。
冥冥之中,一切早已埋下伏笔,只是当时尚不自知罢了。
午后三刻,狐仙被褫夺仙号,下罚天牢,听候发落。
彼时少年刚从兔宫的层层华帐后醒来,他做了一个悠长空白的梦,睁眼时还是茫然的,愣愣看着立在床前的一圈人:“爹,娘,大家……你们都围着我做什么?”
他娘亲忽然抬起手捂住脸,呜呜地哭了起来,连父兄也是满面慨然。
少年撑起身,金线绣着大片牡丹的丝绸软被从他身上滑落,一头乌发披在肩头,还是弱冠时的稚嫩模样。
“恭喜兔仙大人,恭贺兔仙大人!”族长苍老的声音传出殿门去很远很远,“病愈安康——”
少年吃了一惊,他想自己不过是睡个午觉而已,怎么倒成了生病?
娘亲忙道是他中秋夜里饮酒,受了凉,烧得迷迷糊糊的,睡了一天一夜才醒来。
“是吗?”少年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喃喃自语道,“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打这一日起,他回归主位,继续与年迈的族长和父王一同料理族中大小事务。
人人都说,兔仙同以前一样,脾性温和,做事妥当,井井有条,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心里总存着些疑窦。
先是起初那几日,爹娘怎么说也不肯让他照镜子,殿里上上下下,包括兔丫鬟的小镜都收了去。
起因是他发现自己长得相当快,一日在他这里几乎等同半年,头发和指甲不过一盏茶时间便要赶紧剪一次,四肢也在抽条,睡了一夜后站起来,额头直接撞到了床顶的横梁。
其二,他们族人本就可以任意维持兔形人形,只有他每一变化就觉得难受,化成人形走得极别扭,变回兔子方才觉得舒坦几分,明明之前从未有过这种感受。
放水时他都避开人,化成兔形撒完了再回来,不然总觉得别扭。
最后一点,他总会做些奇怪的梦,梦里有一个模糊的影子,只依稀记得似乎尾巴极大,有时他们在一起玩乐,有时他们在一起睡觉,尾巴勾着尾巴,像是感情极好的样子。
这些梦来得离奇,可是只要前一晚做了这些梦,第二天他的胸口就酸涩不已,魂不守舍,好像把很重要的事给忘了。
他也想当作自己只是睡了绵长一觉,中秋夜宴,他初列仙位盛情难却,便纵情饮了几杯,可那之后……那之后真的什么事也没发生吗?
有几次,他看到胞弟望着他,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心里那个未解的结便愈发梗塞起来。
几百年的前尘旧事如香断烟尽,无人提起,他也不再记得,把那人一并忘记了。
三月里一个春日天,天宫大办赏花会,众仙浩浩荡荡从天河头坐到天河尾,曲水流觞,和风煦日下十分雅致。
白兔席间被王八大仙倚老卖老连灌六杯,等赏花会结束时已双颊绯红。他急着回宫,上了轿才走一段,斜刺里忽然冲出一只绿眼小狐。
轿旁两个守卫忙拿剑戟去叉它,它倒很灵巧,骨碌碌三翻两滚站定了拦在路上,毛还蓬乱着便冲着轿子破口大骂:“卑鄙小人!你给我滚出来!”
守卫怒道:“哪来的疯狐狸!”说着扬手便要狠抽他一鞭。
白兔立时撩开纱帘喝道:“慢着!”
那绿眼小狐毫不在乎悬在头顶的厉鞭,显然抱定了视死如归的决心:“大人明日就要被流放,你还有闲情逸致坐在那里饮酒作乐!真是毒辣!什么兔仙,我呸!忘恩负义!我早知道,你的心比石头还硬!”
白兔眼看小狐说得头头是道,心里渐渐有根弦绷了起来,却仍旧很茫然:“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谁要被流放?”
绿眼小狐定睛瞧了他一眼,也看出些不对头:“你莫非真忘了?百物包袱,蟠桃粉镜,狐狸殿里听着雀竹曲睡觉……”
看着白兔的神情,小狐越说声音越小,脸色也彻底灰败下来:“大人对你那样好……原来全不作数了。”
到这般田地,哪怕挣得粉身碎骨又有什么意义?它垂头默然片刻,道:“若你还有半分惦念,明日午后便来混沌镜送大人一程,他要被堕放人间了。”
说完这话,小狐便径自转身离开,蓬乱的尾巴垂在地上,毫无生气。
白兔脑袋里乱成了一团,只觉头痛欲裂,待回到宫殿里,酒意正酣,沾着床便睡了过去,梦里片段纷杂,却总有个很低柔的声音在唤他,一次一次,耐心地,带着轻轻笑意,似乎连念他的名字都觉得欢欣一般。
他不断地向前走,黑暗里忽地亮起一双红瞳,火似的把整个梦境都烧着了,楼宇塌陷,那双瞳仁却圆了亮了,微微笑眯起来:“念舒。”
前尘悠悠,好似悠远笛声中一桩清梦。
“念舒,与我共饮一杯可好?”
桂香十里,正是许多年前中秋时节,那狐狸借着一点酒意,一路穿过神仙们走到他身边,小心翼翼地问出这句话。
那时天宫里人人都传狐仙喜欢兔仙,还有扎双髻的仙童打趣说“兔仙袍下风流狐”,悄悄地将他们编排到一起。
他知道为什么——狐仙五岁多时被黄大仙的小儿子扑在地上撕咬,眼看快奄奄一息,他虽然害怕,却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把小狐仙救了下来。
打那之后狐仙便常常来缠着他,他分明拿他作弟弟,可狐仙长到十几岁时便纵览诗书,谈吐间气宇轩昂,让他简直没法再随意对他。
他还记得有人讥笑狐狸缠着自己不放,狐狸听了也不恼,仅摆一摆尾巴,浅笑道:“我是来向念殊报恩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份恩情也随着他们年岁渐长,渐渐变了味道。
才想到这里,梦中的自己已经与他碰杯:“今年是你弱冠之年呢。”
狐仙怔了怔,微笑:“你记得。”
“这是当然。”
狐狸的大尾忽然猛地摇了摇,都碰到他背上才察觉过来,生生打了个卷往回收:“念舒,我……我有话同你讲。”
“你说。”
狐狸紧张得险些把白玉杯捏碎,恰逢有个小侍童走过来,他便吩咐:“再拿些酒来。”
他因笑道:“到底什么事,还要喝酒壮胆?”
其实他心里也有数,七上八下个不停。
那侍童去了老大一会儿才回来,捧着一只琉璃酒瓶子,一语不发地为狐狸满上酒,很快便退了下去。
他们并不知道那侍童退到暗处,一把将脸上血淋淋的人皮掀了,顷刻露出一张长嘴尖牙脸。
黄皮子伸出舌头,阴森森舔了舔脸上还热乎的血。
那边狐狸一口饮了那杯酒,斟酌了很久才道:“念舒,我从小便想着,等到了能谈婚论嫁的仙龄,一定要立刻向你表明心意,求你嫁给我。”
“我又不是女子。”他被他定定瞧着,耳朵也热了,“什么嫁不嫁的……”
他们坐在天河边上,河面上盛着一圆波光粼粼的月亮,远处众仙在欢饮起舞,感觉像看特别远的一份热闹,而给他们独留出一寸寂静。
似乎酒意上来,狐狸有些热了,揪了揪胸前的衣襟才道:“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故意作不知道的模样?我小时候努力学琴,只为了能有理由去你殿里请教;后来看那么多书,就为了能和你平起平坐地说一句话,免得你和鹿仙他们聊天时我一句也插不上;我努力学画,学成后才敢画你,画的也全是你,一张又一张堆在书房里;我——”
他正听得怔然,狐狸忽然喘气急促起来,焦躁而疑惑地皱了皱眉:“我这到底是……”
那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哗啦一声巨响,一条银色小鱼被吓得卷尾跃出水面,而他被摁倒在冰凉的河水里,脖子上深深嵌着他的犬牙。
哪怕是在回忆的梦境中,他仍旧一瞬间窒息了。
他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目光迟钝地从那轮圆月滑到压在自己身上的狐狸脸上。
眼看着自己的皮被撕裂,血肉被吞食,再诡谲没有的画面,他嘴里的是自己的肉,那些血顺着狐狸的下巴滴答滴答落回他脸上,粘稠滚烫得吓人。
狐狸变长的指甲在他肩膀上穿了洞,那对总是灼灼的赤红瞳仁此时像两个大火球,野兽,野兽,野兽……要把他整个儿吞掉,连皮带骨。
耳朵被咬住时,他忽然从浓烈的血腥味里嗅到蛇辛药的辣味。
他依依听到远处有尖叫声。
大概是被看到了吧,他被撕碎后一直流血,一直流,几乎把整片河面都染红了。
意识渐渐弥散,在狐狸狠狠撕咬他胸口时,他咬紧牙关用全力抬起胳膊,发现自己的右手已经被他咬掉了。
他用残缺的肢体紧紧抱住狐狸的头,对方还在啮噬他的骨肉,他竟丝毫不觉得可怕。
“你莫,莫要,”他磕磕绊绊地开口,因为喉咙全被咬破,说话时都带着血沫浮腾的声响,“……怪自己。”
石破惊天一声巨响,念殊猛然惊醒——天光大亮了。